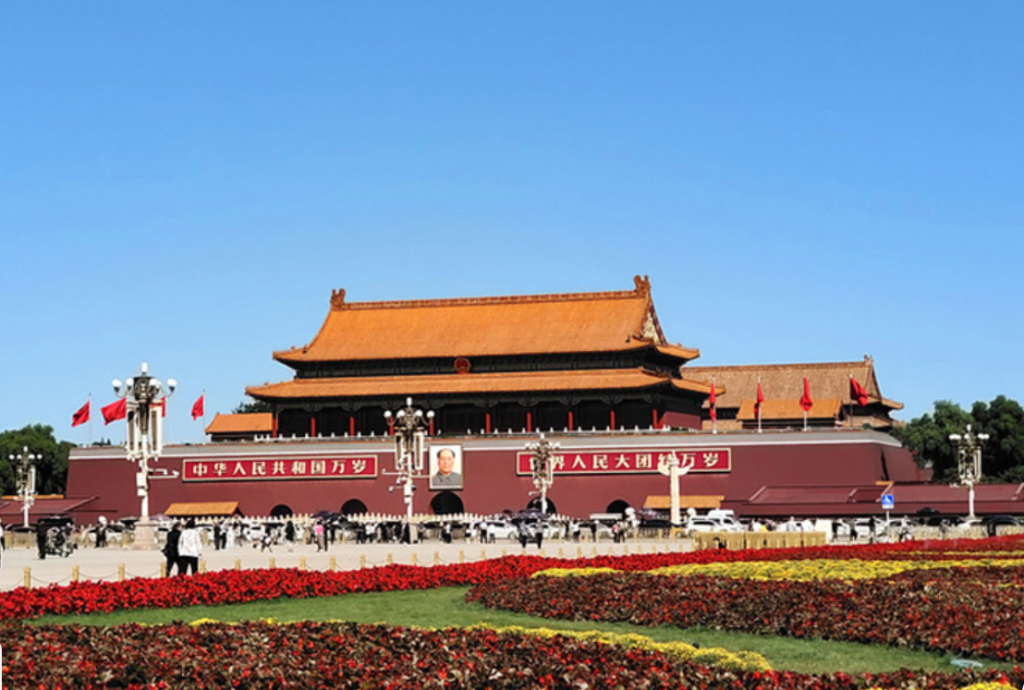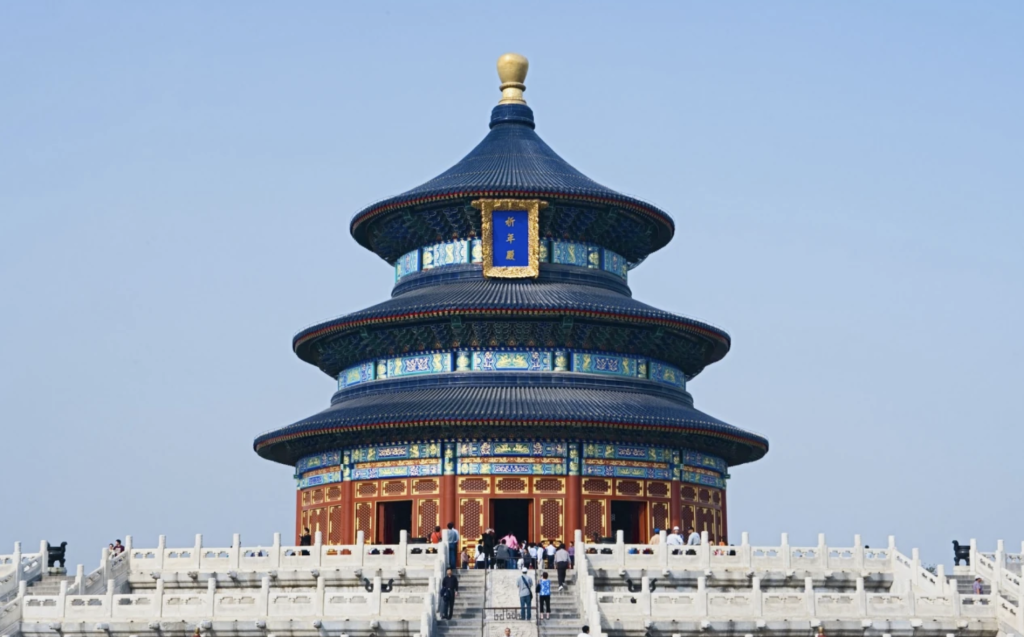李成:“工程师治国”与“律师当政”——中美发展路径的差异

(编者按:本文的英文原版由《南华早报》于2026年2月12日发表。本文的中文译本在英文原版基础上进行编译。作者为李成和赵修业。本文的中文版转发自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谁来治理”这一治国理政永恒的问题在当今中美竞争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随着这两个大国展开激烈的竞争,中国的“工程师治国”模式与美国的“律师当政”模式之间的对比,正在塑造两国各自的政策制定过程和发展路径。
中国将于今年批准并实施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并设定2026-2030年的发展目标。“十五五规划”期间,中国将优先推动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业整合。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执政一周年之际已经面临超过600起法律诉讼,并试图削减哈佛大学以及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等科研机构的资金。在美国政治体制中,法庭日益成为政治斗争的竞技场。中美两国治理风格存在显著的不同,而这一现象充分显示了政治精英的专业背景如何影响其治理方式。
近期我们所在的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发布了“中美高层人事观察”(China-U.S. Leadership at a Glance)数据库,其中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部376名委员与候补委员,和美国174名领导人(内阁成员、参议员和州长)。数据库揭示了中美两国高层政治精英在教育和职业背景方面的显著差异。
通过中美政治精英数据比较,能够明显地看出“工程师治国”在中国的主导地位。这类官员也被称为“技术官员”,即在工程或自然科学领域接受过专业培训、拥有职业经验的政治精英,他们在中国政治领导层占有重大份额。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中有81名技术官员,相当于委员总数的39.5%。
技术官员在中国政治精英中的比例从2007年中共“十七大”时期曾逐步下降,但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后开始回升,并且达到将近20年内的新高。这一变化再次体现了“工程师治国”与科技创新在中国的战略地位。从专业背景上看,中国的第一代技术官员大多主修电气、水利工程和土木工程,如今的“技术官员2.0”则拥有人工智能、半导体、航空航天、环境科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学位。在美国不断加强出口管制的背景下,他们致力于推动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争取实现技术自主。举例而言,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曾担任中国探月工程总指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原中央网信办副主任曹淑敏是通信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
相比之下,美国政治体系中科技背景领导人的欠缺令人印象深刻。在高层政治领导人(内阁成员、参议员和州长)中,只有5人(2.9%)获过工程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本科或以上高等教育学位,并拥有科技领域的从业经历。他们基本都在职业生涯早期从事相关领域工作,但很快投身商业或政治。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利亚(民主党)在1994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曾短暂担任飞机工程师,但他在1999年就宣誓就任洛杉矶市议会议员。蒙大拿州州长格雷格·吉安福特(共和党)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三年,随后于1986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并在八年后售出其经营的公司。
中国政治精英中技术官员的数量可以追溯到他们的本科和研究生学历背景。中国领导人中学习过工程与自然科学专业的比例是美国领导人的三倍。另一方面,拥有法律学位的美国领导人数量是中国领导人的6倍。几乎一半的美国政治精英拥有法律高级学位,且绝大多数人在投身政治前从事过法律工作。
美国政治领导人对法律而非工程和自然科学的兴趣也体现在他们的学位背景中。只有5名美国政治精英(2.9%)拥有博士(PhD)学位,而46.5%的人拥有法学(JD)学位。另一方面,153名中国政治精英(40.7%)拥有博士学位,只有14人(8.5%)拥有法律学位。在博士学位持有者中,35.9%完成了全日制博士学位,64.1%获得了在职博士学位。20届中央委员中拥有博士学位,以及完成全日制博士学位的比例均创下历史新高。
虽然法律培训有助于强化程序正义,但律师在美国政治中的比例过高也往往增加了政治极化和政策出台僵局。律师背景的官员通常会在行使权力时强调对抗性和程序性。美国国会议员中缺乏技术背景的官员,因此限制了立法者对前沿技术问题的理解。即使在参议院商务、科学和交通委员会中也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是技术官员。政治精英内部专业科技知识的缺乏导致政策制定很容易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美国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通常选择在科技公司或投资公司任职,而非进入公共政策和行政部门,导致政府中技术官员的缺失。
相较而言,从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中国在过去40年里培养并提拔了几代技术官员,实现了科技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总体来看,技术官员务实且纪律严明的决策使中国成为创新中心和制造强国。
虽然没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但主政者职业背景的平衡可能是中美两国未来科技和实力竞争的关键。在美国,随着特朗普总统呼吁振兴制造业,如能培养更多工程师和科学家并将其提拔进入政府高层将是正确的一步。对于中国而言,加强法治建设也符合政府在2035年实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长远来看,中美两国这两种不同治理模式的长期影响,只能通过它们的治理绩效,以及它们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来评估。
作者
-

李成是香港大学政治学教授。曾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兼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和美国百人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