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国际安全》期刊:中国想要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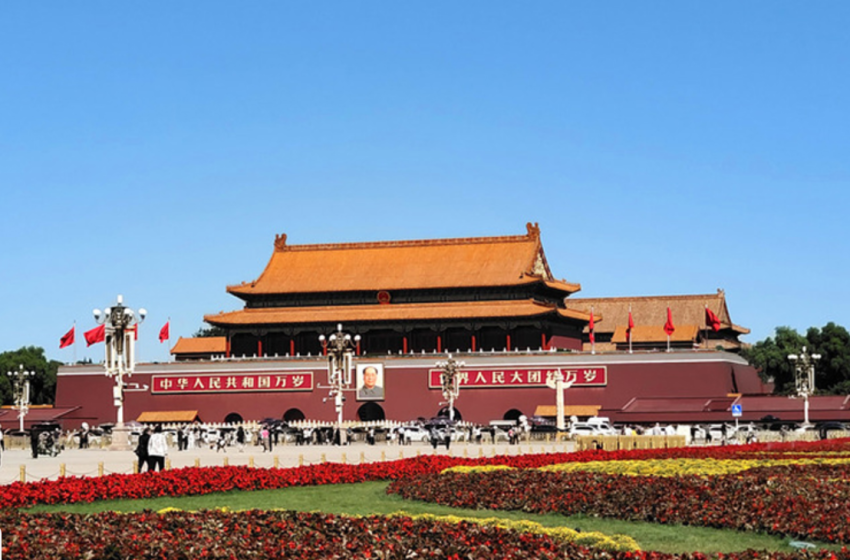
[编者按:由David C. Kang, Jackie S. H. Wong, Zenobia T. Chan三位学者联合撰写的一篇题为《中国想要什么》的学术论文近日由著名的《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出版。该论文分析了上万篇中文文章以及习近平上百次讲话,通过大数据来论证中国是一个更关心维持现状的国家,而不是某些分析人士所强调的希望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霸主的国家。我们把该文的摘要和结论部分翻译发表出来以飨读者。文章加粗部分为编辑所加。阅读全文,请点击。《国际安全》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出版,由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赞助并编辑。]
摘要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霸权国家,渴望取代美国、主导国际机构,并按照自身意愿重塑自由国际秩序。本文通过对12,000篇文章和习近平数百次讲话的分析,以辨析中国的意图,聚焦于中国话语中的三个关键词或短语:“斗争”、“东升西降”,以及“无意取代美国”。研究发现,中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国家,更关心政权稳定,内向性大于外向性。中国的目标明确、持久且有限:关注的是边界、主权和对外经济关系。其主要关切几乎全部是区域性的,涉及香港、台湾、西藏和新疆——这些地方在区域范围内均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本文的论点有三点主要启示。第一,中国并未构成传统观点中所宣称的那种军事威胁。因此,美国在太平洋采取敌对的军事姿态是不明智的,并可能不必要地制造紧张。第二,中美两国在一些被忽视的领域可以开展合作。第三,传统对华看法忽视了经济和外交领域,而这些领域并不适合以战争为核心的战略方式。
西方对中国有许多令人担忧的地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2万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17万亿美元。过去一代人中,中国实现了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并迅速增加核弹头储备。中国每年在国防上的支出接近3000亿美元。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巩固了权力,似乎将长期统治这个威权的共产党国家。中国企业常常从事一些存在争议的行为,例如限制数据、不严格执行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网络窃取。中国政府侵犯人权,限制公民的诸多自由。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各国都在东海和南海争议岛屿进行填海造地并推动军事化。简言之,中国对美国乃至世界构成了许多潜在问题。
在美国学术界和政策制定圈中,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意在称霸世界并扩张领土。例如,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第二任期的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写道:“如果中国能够征服台湾,那么它就可能将目光投向更远的目标……一个自然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菲律宾……越南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也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目标。”拜登政府中国和台湾事务副高级主任、拜登对华政策的关键设计者杜如松(Rush Doshi)则认为,中国一直在打一场“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持久战。布什政府时期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政策规划主任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警告称,中国正在“扩大领土主张”,并积极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与科技国家,并在东亚取而代之”。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则认为问题在于“亚洲的地区霸权:中国希望获得这种地位……并利用该地位对国际现状进行重大修改。”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与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断言,“虽然北京肯定愿意打压越南,但一个更诱人的目标是菲律宾,它符合成为理想敌人的全部标准……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一项宏伟计划,要改写亚洲乃至更广范围的全球秩序规则……它希望成为超级大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022年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日益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特朗普时期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声称:“在我看来,中国是对美国的生存性威胁……中国把自己看作世界第一,并且想要保持这种地位。”
这些对中国意图的判断,使得美国主流学者与政策分析家,无论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都提出了长远的政策方案,几乎完全聚焦于备战、威慑与对华脱钩。相信“中国威胁论”的人呼吁美国增加军费开支,并向中国展示“决心”。传统观点还主张扩大地区联盟,不论伙伴国是民主还是威权政体,只要愿意联合美国共同遏制中国即可。正如科尔比所写:“这是一本关于战争的书。”布兰兹与贝克利认为,美国应当加大力度威慑中国入侵台湾:“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项战略,以在2020年代威慑甚至赢得一场冲突……五角大楼可以通过把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变成一座‘死亡陷阱’,大幅提高中国发动入侵的代价。”杜如松则主张,美国应当武装“台湾、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以遏制中国。
这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究竟想要什么?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从中国的言论与行动出发,探讨当代中国的目标与担忧。与传统观点相对比,本文提供的证据得出一个总体结论和三个具体观察。总体而言,中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国家,关心的是政权稳定,内向性大于外向性。更具体而言:第一,中国的目标明确;第二,中国的目标具有延续性;第三,中国的目标有限。
首先,中国的目标明确:中国关注边界、主权以及对外经济关系。它关心在东海、南海以及与印度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几乎所有的关切都是区域性的。其次,中国高度重视对各个已被区域普遍视为中国一部分的地区的主权,包括香港、台湾、西藏和新疆。第三,中国在处理与东亚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方面,有着越来越清晰的战略,其目标是扩大贸易与经济关系,而不是削减。
同样清楚的是,中国不想要什么:中国话语中鲜有关于全球领导或霸权的宏大目标或野心。此外,中国并未输出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强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普适的世界模式。相比之下,美国声称代表全球价值和规范。中国同样不想做的事情包括入侵和征服其他国家;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对其边界之外、或区域内不在其主权声索之内的国家构成生存性威胁。
本文还探讨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在区域及全球中的位置与角色。鉴于公开声明的权威性存在差异,我们主要考察了三个来源:《人民日报》(既代表国家,也代表中共中央)、习近平及其他高层官员的讲话,以及中共发布最新政策导向的《求是》杂志。我们采用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方法,对中国表述的目标进行系统性评估,以更准确地追踪中国的关切并识别其变化。同时,我们还发现,中国高层始终反复强调,中国无意谋求地区霸权,也不打算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相反,中国将国际关系视为多边和合作的。
其次,中国的目标是历史延续的,而非新近产生的。中国存在一种“跨朝代”的身份认同:几乎每一个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关注的重大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清朝时期。这些并不是1949年共产党建政之后才出现的新目标,中国的核心关切也不是习近平才提出的。这些都是延续至今的中国关切,尽管在过去两百年间,中国的政治权威经历过数次剧烈变迁。
第三,中国的目标是有限的,即便其实力在过去一代人中快速增长。中国的诉求和目标要么已逐步解决,要么保持静态。这一现实与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许多预期,以及国际关系学界的传统观点(即国家利益会随着国力增长而扩张)形成对比。相反,证据表明,中国领导层更关注内部挑战,而不是外部威胁或扩张。
我们发现,中国并未构成传统观点中所宣称的那种军事威胁。因此,美国没有必要在太平洋采取敌对的军事姿态,事实上,美国可能正在不必要地制造紧张。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建议两国在许多当前被忽视的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最后,传统对华看法淡化了经济与外交领域,而这些领域并不适合以战争为核心的战略方式。美国大战略中的主流认知存在问题,华盛顿对中国的想象是危险地错误的。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回顾美国高层政策制定者与现有学术文献中关于中国目标的传统观点。第二部分分析中国话语,并指出解读其中细微差别的方法。第三部分使用量化方法,更系统、准确地评估中国在最具权威性表述中跨时间的诉求。第四部分阐述中国的主要优先事项如何具有延续性和跨朝代特征;第五部分则表明,尽管中国国力快速增长,其最重要的诉求并未扩张。最后,我们在结论部分提出本文对中美关系的启示。
结论
理解中国想要什么,是制定一项成功且持久的对华及对整个东亚地区政策的核心。当前,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学界的主流观点对中国持悲观态度。在这种视角下,中国被视为在领土上雄心勃勃、在经济上具有威胁。然而,其中许多论断所依赖的证据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对现有证据的仔细审视使我们得出结论:中国主要关注的是政权安全(如国内稳定,以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国远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和雄心勃勃的大国,其利益是清晰的、持久的、且有限的。
我们研究所得出的最重要的启示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没有必要维持一种敌对的军事姿态。中美两国有许多问题需要谈判——与中国企业打交道可能会很困难,中国政府可能会强硬固执,而美中在许多重要议题上存在分歧。然而,这些摩擦都是国际政治中的常态,并不需要美国在未来数代人中持续聚焦于战争准备、威慑和经济脱钩。事实上,这种战争导向的聚焦反而有害于解决两国所共同面临的外交、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高风险问题。难以想象,诸如人权、民主、气候变化或移民等议题能够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
我们的研究所得出的第二个启示是:中美在许多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例如: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再生能源转型、减少污染以及为大流行病做准备。例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就曾启动项目探索合作可能性。该项目咨询委员会主席指出:“在健康、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等领域实现具有颠覆性影响的机会近在眼前,但这些机会将取决于能否建立新的机制和叙事,使中美能够开展合作。” 因此,美国国内确实存在一定的开放态度来探索合作,但这种态度往往被主流的“遏制中国”观点所掩盖。正如科尔比(Elbridge Colby)所写:“读者在这里不会找到关于如何与中国进行经济竞争的任何讨论。”
最后,当前主流的美国政策建议——即对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和经济遏制——尤其令人担忧,原因有二。第一,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创新能力远超许多人的认知。第二,东亚地区存在多项稳健的贸易和外交倡议,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东盟(ASEAN)。CPTPP 于 2018 年签署,目前有 11 个签署国,另有 9 个国家已经申请或正在考虑加入。RCEP 于 2020 年签署,它是东盟 10 个成员国与 5 个伙伴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而美国并未参与这些倡议。如果美国希望保持其作为区域和全球领导者的地位,那么它理应参与这些区域与全球治理机制,而不是选择退缩。2025 年初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关税政策虽显极端,但与主流的“对华脱钩”观点是一致的。即便特朗普此后降低了部分关税,总体关税水平仍远高于数年前,而且未来很可能再次上调。
然而,考虑到中国在创新和追赶美国方面的惊人速度,贸易壁垒可能并非最佳的长期大战略。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无法深入讨论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但可以肯定的是,贸易限制和关税似乎已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默认政策,至少目前如此。随着东亚国家不断加深与中国的互动,这些举措将是一个重大错误。例如,在特朗普 2025 年 3 月宣布关税政策之后,习近平应邀宣布将访问越南;中、日、韩则举行了五年来的首次三边峰会,并宣布将进一步探讨建立三大经济体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通过误解中国的真实意图,美国有可能在不存在问题的地方制造问题,并在东亚被边缘化,从而损害其自身的长期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