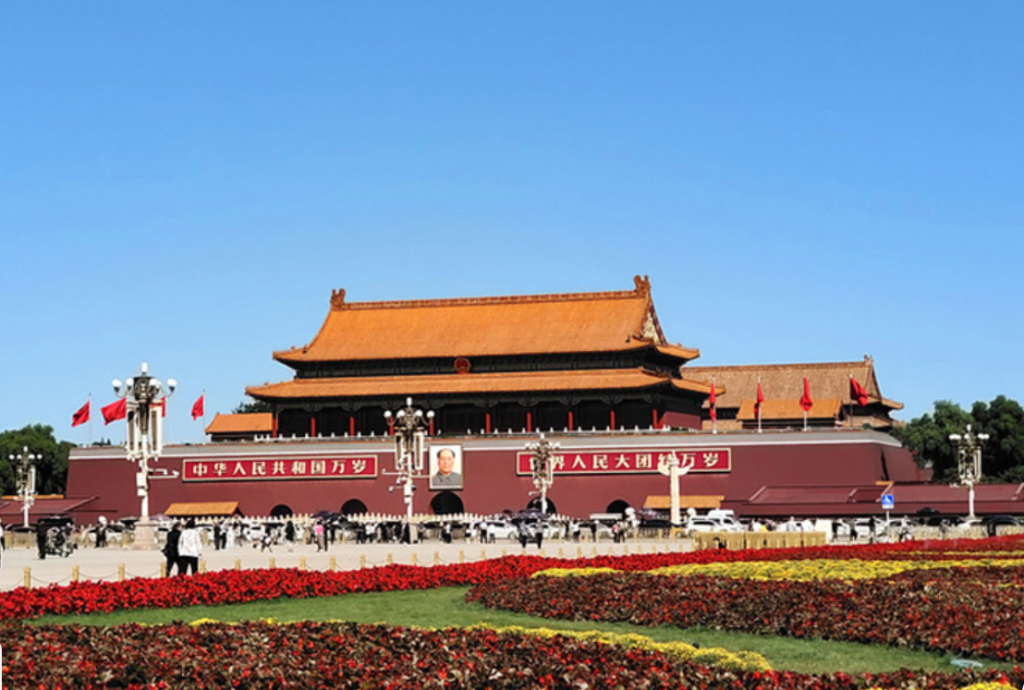专访 | 文安立:中国改革的非必然性——1970年代的混沌与“错失的机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70年代是相对鲜为人知的一个时期。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顶峰已经过去,但80年代的改革尚未开始。1970年代这个关键而又模糊的十年,正处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即将定义21世纪中国的市场改革萌芽之间。
在由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和陈兼(Chen Jian)两位冷战史领域的领军学者合著的《大转型: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之路》(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China’s Road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一书中,他们探索了这个至关重要却常被忽视的十年。通过对众多学者、官员、记者、商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的访谈,他们揭示了1970年代如何播下了市场转型和政治自由化的种子——这些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从草根层面展开的。
这挑战了将国家的转型完全归因于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层决策的官方叙事。相反,韦斯塔德和陈兼表明,正是普通的中国人民站在了变革的前沿。他们强调,中国的经济改革作为一个历史结果,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预先注定的,1970年代代表着国家未来仍有多种可能路径的时刻。
中美印象采访了韦斯塔德教授,以更好地理解1970年代的中国——一个充满可能性、权力斗争以及思想和经济活力的十年。
韦斯塔德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讲席教授,专注于冷战和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兼是康奈尔大学胡适历史学和中美关系荣休教授,也是纽约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历史、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中美关系和冷战国际史。
爱丽丝·刘(Alice Liu): 您将1970年代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与文化大革命和后来的发展时期相比常被忽视的时期。七十年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通过更仔细地研究这一时期可以获得哪些见解?
文安立: 我认为1970年代在很多方面对于中国成为我们今天所知的中国至关重要。文化大革命和20世纪早期动荡带来的变化对许多人来说是灾难性的。正是在197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逐渐好转,这使得把70年代视为一个单一的十年变得有意义,尽管它是一个异常漫长的十年。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现在谈论的是“长长的1970年代”——从196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中期。
原因在于,所有这些变革过程都需要时间。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在1960年代末就结束了。这场运动的大部分狂热情绪已经消退,早在1970年代初,你就已经看到草根阶层试图改变中国经济的尝试浮现。尽管毛主席和他的激进派圈子仍在北京掌权,但你可以看到,至少在思想上,那种控制力在197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松动。而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后,这种松动就变成了洪流。
到了1970年代末,中国在经济方面已经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社会。五年后,那种向市场、向更大开放、向人民更多参与国家经济和政治运作的改革进程,在很多方面已经根深蒂固。从那时起虽然也出现过挫折——1989年镇压学生运动,以及过去十年转向新形式的威权主义。但到那时,中国历史的基本形态已经以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了。这就是1970年代发生的事情。
AL: 您在书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在68年左右就已经基本结束了,但官方叙事却一直把它拖到76年。您认为这是为什么?人们为什么倾向于忽视或淡化七十年代?
文安立: 您刚才提出的这两个观点是紧密相连的。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领导层希望给人一种印象,即他们是中国的戏剧性变革的推行者。这其中有一些真实的成分——我认为如果没有中央的这些变化,变革不会如此深刻和迅速——但他们不希望人们想到,这些变化很多是来自底层的,来自于那些通过自己采取行动来使家人摆脱贫困和饥饿威胁的人们,他们将权力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这是中国当局普遍不喜欢的。他们更喜欢自上而下的改革理念。1978年通常被视为关键的一年,当时邓小平的开放政策真正得以巩固,至少部分其他改革也被共产党的纲领所确立。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原因。如果你关注更早的那个日期,你也会更加关注来自底层的变革以及社会对文化大革命的反作用而产生的变革——而不仅仅是高层发生的事情。
AL: 您认为中国的改革不一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项目,而更像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为了让我们的读者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哪些社会群体或地区是率先推动变革的?
文安立: 它或多或少发生在全国各地,但都集中在相对较小、有时相当孤立的环境中。不过,重要的是要强调,只有等到北京的政治变革实际发生之后,它才能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现象。但在那之前,那些思考改革的人已经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了。陈兼和我在这本书中使用了各种小型企业或集体企业的数据,这些企业大多建立在沿海的浙江、江苏和福建省,以及南方的广东,它们通常靠近城市但不在城市里。这些通常是在人民公社内部建立的小型企业,它们是集体经营的——不是国有——而是由工人集体或当地人民公社当局经营的。它们开始生产超出计划的、用于普通消费的产品。在严格的中央计划体制下,这些地方会有他们应该完成的一系列目标。
计划经济的运作方式是,你工作到那个目标,然后你就不会再做更多了。而这些人所做的是超额完成配额进行生产,因此他们有了可以出售的剩余产品——当然,这是完全非法的。这在当时,也就是1970年代初,是超出被接受范围的,因此他们往往不能换回金钱,而是换回了可以转卖的其他产品。特别是那些靠近城市的人有很多机会这样做。
渐渐地,这开始货币化,因为如果你在广东——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那么香港也就在附近。早在北京的官方改革开始之前,这些集体企业中的少数就能够通过水路走私一些换得的产品到香港。在一个我们遗憾地未能写入书中的案例中,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涉及保密等问题,其中一家集体企业在1972年或1973年初甚至设法开通了一个香港银行账户。同样,这是严格非法的,但这让他们在中央层面的改革开始时抢占了先机。
AL: 您认为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向早期资本主义的转变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预先注定的。相反,在每一个关头,多种路径都是可能的。您能重点说明一两个关键时刻,如果做出不同的决定,可能会极大地改变中国的轨迹吗?
文安立: 1970年代的中国政局相当混乱,从毛泽东去世之前直到去世后不久,从政治角度来看,谁将在这场进程中占据上风并不明朗。毛泽东长期主导着中国政治和共产党,以至于人们很难想象在他去世后会发生什么。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替代方案。文化大革命左派,毛泽东本人曾支持,但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由他的妻子江青和一个与她密切合作的小组领导,主张一种更激进的革命形式。他们希望远离我们讨论过的所有改革努力,特别是那些来自底层的努力。他们非常、非常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的原则,即中央计划经济。
军队可能是当时最有权势的机构,最终正是他们与左派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以至于在毛泽东去世仅仅一个月后,他们就发动了政变,基本上逮捕了共产党内的整个政治左派。但他们内部也有分歧。军队中的许多人对中国的未来和中国应该走向哪个方向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当时在考虑,中国为什么不回到1950年代的样子——重建一个以苏联为蓝本的模式,这个模式在当时似乎运作得相对良好,而毛泽东后来脱离了它。
毛泽东在外交和战略上都与苏联决裂了。因此,存在着大量的不同选择,而且政治相当混乱。改革派——当然不是邓小平周围的改革派——并不保证能取得胜利。坦率地说,陈兼和我认为,如果没有军事政变,这些人要进入权力位置会花费更长的时间。毕竟,邓小平是毛泽东本人两次清洗过的人,在毛泽东去世时他仍然生活在对生命的恐惧之中。因此,高层局势很容易就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
AL: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本可以很容易地回到中央计划经济,但却没有。他们为什么没有回到苏联的模式呢?
文安立: 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后,党内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在1950年代,当中国共产党刚刚掌权并与苏联紧密结盟并以其为榜样时,情况是相当不错的。毛泽东会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是事情进展得太慢、太谨慎了,必须像他所说的那样,“大步跃进未来”。但在那场运动如此彻底地失败之后,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相当多的人在想,我们为什么不回到那个模式呢?
在我们看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方面。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包括那些持亲毛泽东观点的人——与苏联之间已经在政治上存在着如此多的敌意,以至于很难再回到那里。但另一个原因,也是有点难以理解的一点,是在1970年代末,至少一些掌管共产党的人得出了结论:从全球范围来看,似乎做得最好的不是那种经济发展形式。对中国来说,向那些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学习——而不是仅仅向没有快速增长的苏联学习——将是健康和明智的。因此,向日本、美国,甚至向东亚那些似乎正在经历经济腾飞的小国学习——这是他们没有回到苏联模式的关键原因。
AL: 您会如何描述文化大革命与改革时代之间的关系?改革是一次彻底的决裂,还是如您所暗示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为改革打下了基础?那一部分对我来说特别有趣。
文安立: 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也是一个很难达成共识的观点。文化大革命,在陈兼和我们看来,主要是一项破坏性的工作。至少在它最活跃的阶段,积极的方面并不多。我认为,当你进入1970年代时,左派确实提供了一个与改革时代相抗衡的政治替代方案。但在早期阶段,文化大革命是相当具有破坏性的。我们发现,在许多方面,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就是摧毁了旧中国的许多核心点。它消除了中国发展中许多受中国传统和来自更早时代的中国思想束缚的方面。
想想那些不遗余力地让孩子们批评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政治觉悟不够、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够清晰的做法。在一个中国家庭环境中,这样做的结果是破坏了对长辈的尊重。家庭纽带在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因此,当那个时期结束时,你会发现一代年轻人对大多数事情都相当愤世嫉俗,并且专注于自己如何取得进步,而不是依赖传统、家庭,甚至共产党来取得进步。
这种趋向于自身利益的倾向,具有讽刺意味地,非常适合市场兴起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开始。当然,这不是那些人所想的。这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所想的;他们想要的是相反的结果。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它朝着与最初意图不同的方向发展。
AL: 这有助于为改革做好思想准备。您指出,即使在中国迈向改革的同时,它在叙事和实践上仍然以国家为中心。您如何看待这种“将改革视为拯救国家的方式”与“将改革视为迈向真正社会自由化的一步”之间的张力?
文安立: 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从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层来看,当邓小平和他的追随者在蛰伏一段时间后重新掌权时,他们对中国国家的倒退程度以及共产党因其对国家所做的事情而受到大多数民众的蔑视感到震惊。因此,改革无疑是挽救共产党政权的一种尝试。
他们感到必须实现快速增长——如果不能,他们在内部说——如果不能,共产党就会垮台。这一点非常清楚。他们也愿意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化,这种自由化进展得非常远、非常快。那些年我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看到人们几乎是每周都在为自己争取新的自由,这令人震惊——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言论自由、组织自由,以及所有文化事务、性别相关事务等等。
而且其中大部分来自底层,政府只是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当然,他们不断尝试回滚其中的一些自由——首先是在1980年代中期,然后是在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或之后,这对相关人士来说是灾难性的。但他们从未能够完全做到,因为中国人民已经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也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在这些领域限制得太多,也会影响经济改革的动力。所以这也是他们对回滚持谨慎态度的原因。
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现在的观点是,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发展水平,共产党比以前更容易集中权力和所有活动——确实如此。所以你可以说,改革——这是改革另一个奇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是它最终,在很久之后,使党能够掌握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更彻底的控制权。
AL: 他们认为回滚一些文化自由化会让人们抵制经济改革,这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文安立: 是的。他们担心(如果回滚)将无法实现他们所希望的经济改革程度。因此,这里的想法更多是,许多处于领导地位的人——领导这些改革努力的年轻人——也是重视他们的一些个人自由和能力的人,例如他们的行动能力,或公开说话的能力。如果对这些方面进行全面镇压,那么他们进行改革所需的人才就会变得幻灭,或者试图移居国外或采取非常不同的行动,这样就很难完全镇压。所以这超出了我们的时间范围。
但最好的例子是1989年镇压之后发生的事情。即使在那时,党的领导人也很快向人们保证,这是一次针对他们视为反党、反国家分子的镇压,并且他们会努力将改革推回到1989年之前的状态。当时党内的一些保守派试图利用这一点来推翻自1970年代末以来所采取的大部分方向。但正是邓小平本人和与他一起工作的人表示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肯定会实行政治专政,但在那个框架内会接受某些自由。
AL: 围绕改革这个话题,您在结论中写道,七十年代也是一个“错失机会”的故事,尤其是在政治改革方面。如果您必须点出最塑造中国后来轨迹的一两个具体错失机会,它们会是什么?
文安立: 首先,这与政治和社会自由有关。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本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中国,一个保障人民可以更公开地表达意见、更公开地组织起来的权利的中国。即使在建立这些自由的情况下,共产党的主导地位也不一定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党内有这样思考中国发展的人——党内有相当多的人。在我看来,另一件本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事情是,允许更多空间让人们从底层建立自己的组织。
因此,即使共产党可能不会接受政治竞争——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我认为这在当时是不现实的;但认为他们不会允许在地方层面出现不同类型的治理工具,更多地受到当地民众影响来实际管理中国社会的较小部分,则是不现实的。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应导致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中国。它最终本可以削弱共产党的全部权力,这会是一件好事。我认为这是他们对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如此谨慎的原因之一。
但这会造就一个更好的中国。这会造就一个人民更自由、能够表达自己想法的中国。而那些说——包括今天在西方也有很多人说——“嗯,这行不通,因为中国会过于混乱,无法创造它所拥有的那种持续的经济增长,”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的意思是,看看该地区其他在变得更加民主的同时也实现了强劲经济增长的国家:日本、韩国、台湾,不胜枚举。那种认为中国应该永远被判处独裁统治,仅仅因为它服务于经济目的的观点——我们不接受这个论点。陈兼和我认为这不是事实。
作者
-

Alice Liu是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实习生,在埃默里大学攻读历史学和女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