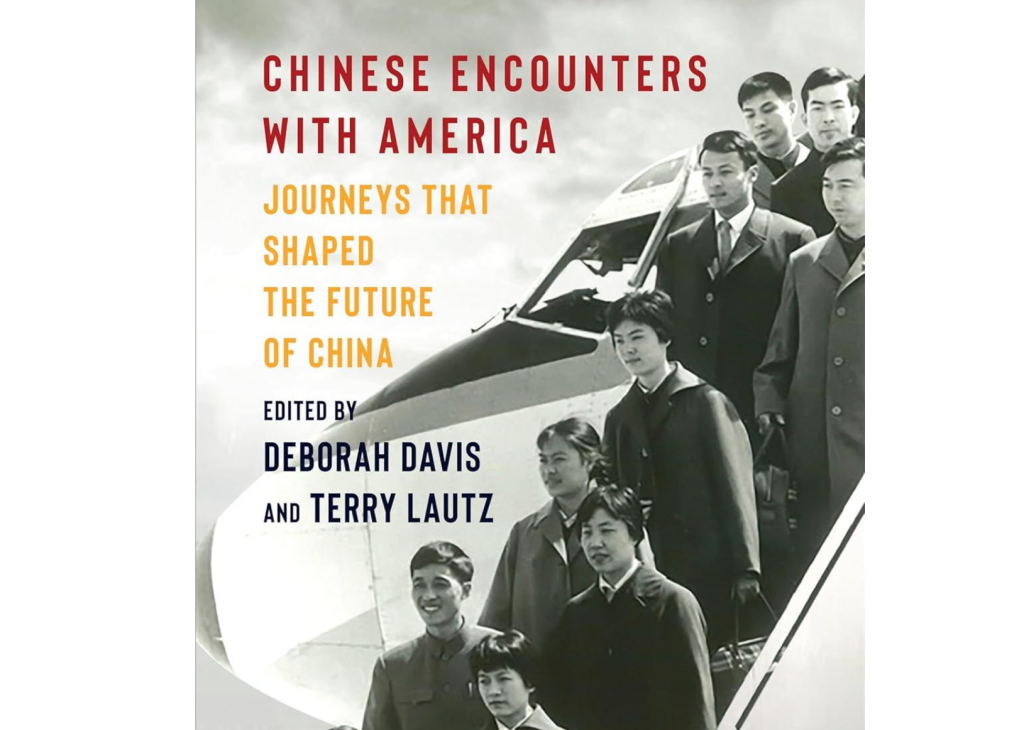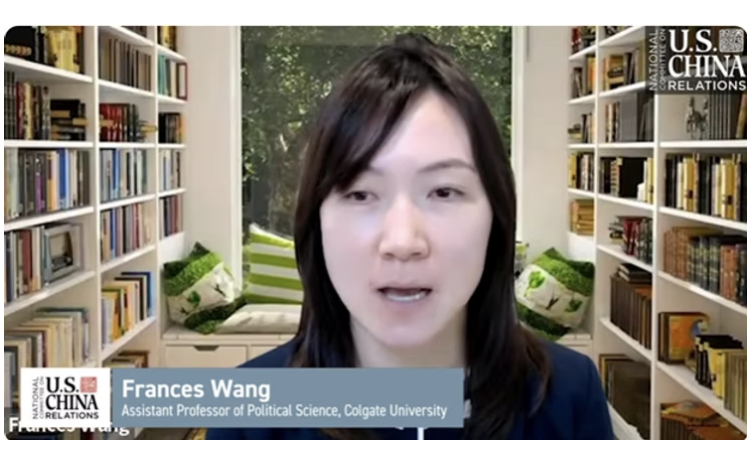专访德雷尔(Jacob Dreyer):住在上海 观察中国社会变迁
- 采访
- ZHANG Juan
- 08/07/2025
- 0

(图片来源:摄图网)
【在2024年7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引发热议的评论文章,标题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开始更像中国》(Trump’s America Is Beginning to Look More Like China,点击这里查看该文中文)。作者是常年旅居上海的美国人雅各布·德雷尔(Jacob Dreyer)。
德雷尔自2008年起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城市变迁有深刻体会。在本次专访中,他谈及撰写此文的初衷,以及他如何看待中美在人工智能、经济挑战、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共性与分歧。他还分析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并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旅居中国的美国编辑,如何跳脱“亲中/反中”二元框架,尝试在中美认知鸿沟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
您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开始更像中国》引发了不少讨论。您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什么?
雅各布·德雷尔(JD): 今年2月我去了一趟华盛顿,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硅谷与特朗普之间的融合(现在大家谈论得少了)。我发现很多现象让我联想到中共二十大之后的中国政策。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还在一些场合做了演讲和讲座。由于《纽约时报》的编辑流程比较漫长,这个想法花了几个月才以他们希望的形式呈现出来,最终发表。
自2008年以来,您一直生活在上海,亲身见证了中国的转型。有没有某个观察或经历,最深刻地影响了您对中美关系的理解?
德雷尔: 我刚离开美国时,感觉美国是个“无聊”但安全的地方,而中国则是混乱、无政府、充满活力的。当时随处可见的腐败、遍布城市的红灯区、疯狂的地下夜生活,以及不断翻腾的社会,让人觉得中国是属于冒险者的地方。
如今,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反而觉得上海成了那个“安全而无聊”的地方,而美国则变得混乱、无政府、腐败当道……。上海从一个“疯狂又野性”的城市变成一个新加坡式、中产阶级色彩浓厚的城市,这种变化我始终铭记于心。但二三线城市的转变,也许更值得注意。
我刚来中国时,很多东西我想要却很难找到——比如咖啡或者牛油果——只有北京或上海的某些地方才有(比如乌鲁木齐中路上的那位有名的“牛油果阿姨”)。如今,这些东西在贵阳、大庆也随处可见了。但或许最显著的变化,是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从过去三成是创业者、七成是工人/农民,到现在逐渐变成一批白领工程师和他们的中产阶级子女。
您在文章中指出,“美国曾是中国工业和消费繁荣的榜样”。在您看来,如今中国在哪些方面仍在借鉴美国?又在哪些方面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德雷尔:中国对美国私营部门的创新仍然高度关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方面;同时也非常重视美国政府在扶持企业(如Palantir)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包括哈佛、斯坦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高质量的机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美国像一家超级市场,提供成千上万种选择,那么中国就是挑三四样喜欢的,其余的则视而不见。
我不确定是否应该说中国“走出了自己的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当美国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放任自流、追逐短期利润时,中国在科技公司监管方面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径。
当然,在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已是全球领跑者,是独一档的存在,不仅为自身,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转型参考(请阅读我去年12月代表威尔逊中心前往印尼的考察)。
您在文章中提到,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自动化以及经济不安全感方面有着共同的焦虑。这种相似性是否为两国合作创造了某种契机?
德雷尔:当然有。有传言说特朗普总统计划在今年9月携美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中美之间本就有很多显而易见的合作空间。而像福克斯前新闻节目主持人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这样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代表人物最近刚刚访问中国,也在公开表示赞同合作。在我看来,由于MAGA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多趋同点,达成协议只是时间问题——不仅仅是贸易协议,也包括安全领域的协议,比如更新版的 “上海公报”。
不过,也有一些中国人认为,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多变、不稳定,难以达成长期协议。我认识的一位上海投资人,甚至已经在展望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上台后的美国了。
您肯定了中国在工业政策方面的远见以及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积极推进。您认为有哪些具体的中国策略值得美国借鉴?而美国在政治或文化上又存在哪些障碍,可能会妨碍这些做法的落地?
德雷尔:所谓“富足议程”(abundance agenda),在我看来,本质上就是试图将中国的一些方法美国化:比如确保监管服务于更大的战略目标,支持关键产业、建设住房等等。不只是战略层面,中国的企业还拥有一些美国目前亟需的工业技能,而这些技能或许可以通过合资企业的形式来引入,比如宁德时代(CATL)与福特的合作就是一个例子。
我希望在特朗普总统和中国达成的协议中,能够看到中国企业与美企之间的合作,通过技术转移帮助美国实现再工业化和脱碳目标。
阻碍并不仅仅来自“监管”这种抽象概念,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体系本身——民主制衡机制会造成推进缓慢和不确定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对其支持者群体有着惊人的掌控力,反而可能使推进合作变得更容易。比如在密歇根州,共和党人曾反对中国投资。如果哪天特朗普与习近平通完电话后,宣布自己达成了一个“伟大的协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么国会里中国问题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穆伦纳尔(John Moolenaar)真的还会站出来反对他吗?
通过将权力集中到行政部门,像中国那样,特朗普可能真的能快速推动与中国的产业合作,让美国重新实现工业振兴。就像当年的尼克松,正因为他曾以“反中”著称,才反而更有空间达成突破。
作为一位住在中国多年的美国人,您如何在撰写关于中国社会的文章时,保持诚实客观,又避免落入“亲中”或“反中”的二元对立之中?在当前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您认为两国之间最迫切需要建立的文化或知识桥梁是什么?
德雷尔:我的生活挺不错的,所以我通常对中国持支持态度,因为我住在中国。很多时候,我与家人的互动,特别是我的岳父母——他们是黑龙江大庆的退休干部——影响了我理解中国政治的方式,他们非常爱国,是共产主义的真正信徒。对我来说,亲中或反中,就像亲冬季或反冬季一样。我们所说的,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早在基督诞生之前就存在了。中国的存在是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去理解它,并决定我们该怎么做(比如,如果我讨厌冬天,我可以搬到洛杉矶)。
数百万中国人曾在美国学习或生活。这种不对称性令人震惊。我认为中国人非常有能力建立他们想要的任何联系。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真的希望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并认识到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哪怕只是为了开始消除这种让美国变弱的不对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