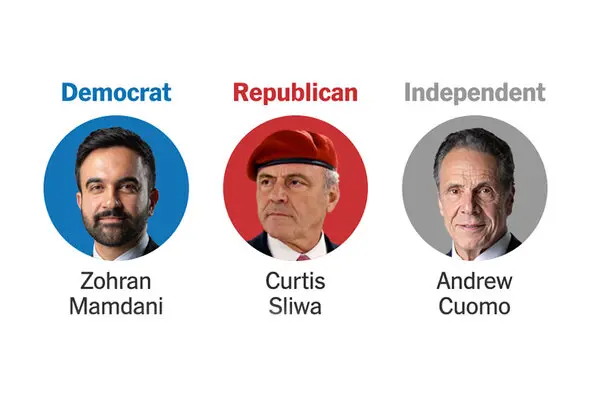美国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下场如何?

作者:邢悦,詹奕嘉 来源:世界和平论坛
在很多国家,政治被视为一种零和游戏,胜者全得,则意味着败者将失去一切:权势,地位,甚至性命。因此,除了获胜,参与者别无选择。在这场压上了性命的较量中,规则就会显得无足轻重。有学者将这种政治文化形容为“全赢全输”,即认定利益冲突、权力之争只有一种解决方式,即“把我们的对手灭了”,否则无法取得彻底胜利,到手的胜利也不会巩固。[1]利益和权力之争也只有一种后果,即“一方战胜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要赢就全赢、不然就全输”,谈判妥协是决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对手和敌人也肯定是这样想的”,所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种思路发展到极端,为了夺取和巩固权力不仅要“杀人盈城”,而且“六亲不认”。
而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政治是一种利益博弈,不需要流血牺牲,而是需要竞争、协商、妥协、磨合以及相关的合法程序。在这种政治文化下,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主要是一种竞争性的对手关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党争要遵循游戏规则,可以通过妥协而暂时平息,对立的各党也可以通过和平方式交替上台,轮流执政。“胜者全得”不会等同于“败者全输”,没必要“抛头颅、洒热血、革命到底”,大不了等两年就是中期选举,再等两年还有总统大选。
在美国,竞争失败者“东山再起”的故事不胜枚举。尼克松在1960年美国大选中以微弱劣势败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八年卧薪尝胆后复出,轻松击败对手汉弗莱和华莱士胜选。
所以,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败者并非意味着永不翻身。在提倡有规则的政治竞争环境中,美国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政治失败者。权力竞争失败是暂时的,失败者仍然具有生存和发展空间,胜利者不可以也没有办法扼杀失败者的政治权利。在美国历史上,不仅仅有像尼克松这样一次选举失败后卷土重来的美国总统,还有许多选举失败后再也没当上总统、却活得更加精彩的政治人物。
吉米•卡特在总统任上政绩平庸、饱受争议,1980年大选中更完败于此前是电影明星、后来是明星总统的里根。但这位任上口碑平平的失败者,在败选后却秀出了精彩人生。他多次斡旋朝鲜危机,在海地和前南斯拉夫政治过渡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媒体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佳卸任总统”。美国政坛有一句经典笑话,就是“卡特败选后比当选时称职多了”。
“败后更精彩”的另一范例,则是2000年“只差一步进白宫”、在普选票中领先、因选举人票微弱劣势败给小布什的戈尔。戈尔败选后逐渐淡出政坛,却在环保领域取得重大成就。2006年,他参与制作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获得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电影歌曲两座“小金人”,2007年更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一起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不知道一直被媒体冷嘲热讽的小布什会不会对曾经的“手下败将”戈尔羡慕嫉妒恨。
那么,那些因竞争失败而没有掌握权力的“在野党”或“反对派”的生存状况又如何呢?
在古代专制独裁政治下,任何与主政者有不同意见的“反对派”都是不允许存在的,如果出现必然被视为“异端”“反贼”,需要镇压和消灭。但在提倡权力制衡的美国政治文化中,反对派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平衡器”,可以警示和制约主政者的行为,使主政者时刻保持清醒,及时纠正施政错误。
在美国历史上,最可怕的“反对派”、最惨痛的“失败者”要数内战中的南方领袖们了。但即便是这些曾经被视为“叛国者”“分裂者”的失败者们,也没有被抄家灭族,更没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美国国会大厦里,陈列着众多雕像,那是国会让每个州送来的本地英雄雕像,每州两座。结果,弗吉尼亚州呈送的竟是两位“叛军”领袖——南方临时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和军事统帅罗伯特·李的雕像。换了在其他许多国家,怎么可能把公然“分裂国家”的“全民公敌”当成英雄来膜拜?可美国国会却照单全收。
连“叛徒”都能容忍,那其他政治上的反对派和失败者只要不违法犯罪,就不再有性命之忧了,连逃亡和流放的都用不着。就算是那些得罪过无数人的从政者,卸职后也罕有遭报复的,更不用说暗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国王,更非独裁者,很少有滥权的机会,政治过错很少被看作“一个人的罪孽”,政治家的安全也不是靠权力系统维系,离开了权力、恢复为常人的他们反而更安全,作为胜利者的美国总统倒是有几个遭遇过暗杀。即便像尼克松那样被起诉,也会面对相应的司法程序,而非极端性的暴力迫害。
来源时间:2016/2/3 发布时间:2016/2/2
旧文章ID:8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