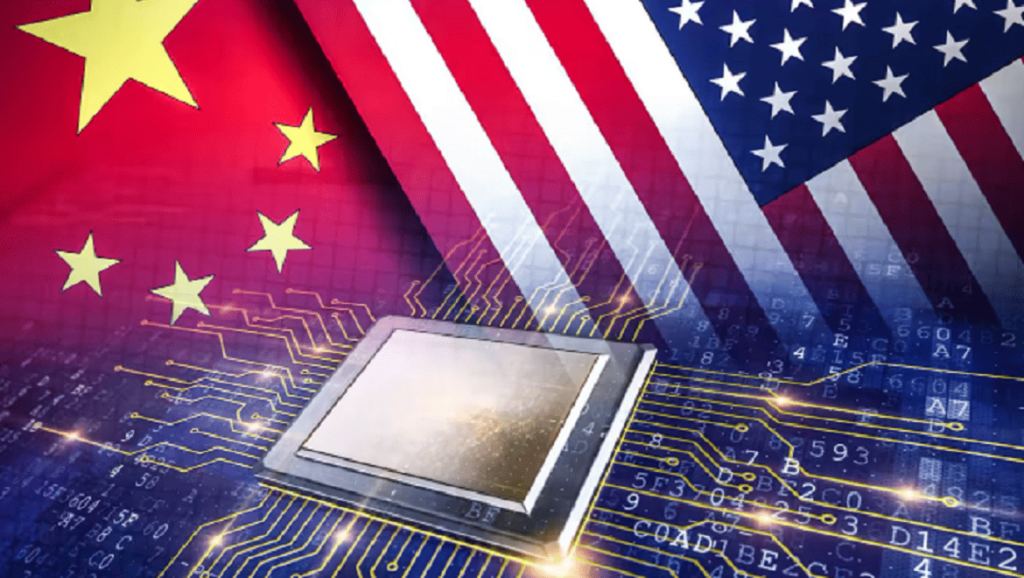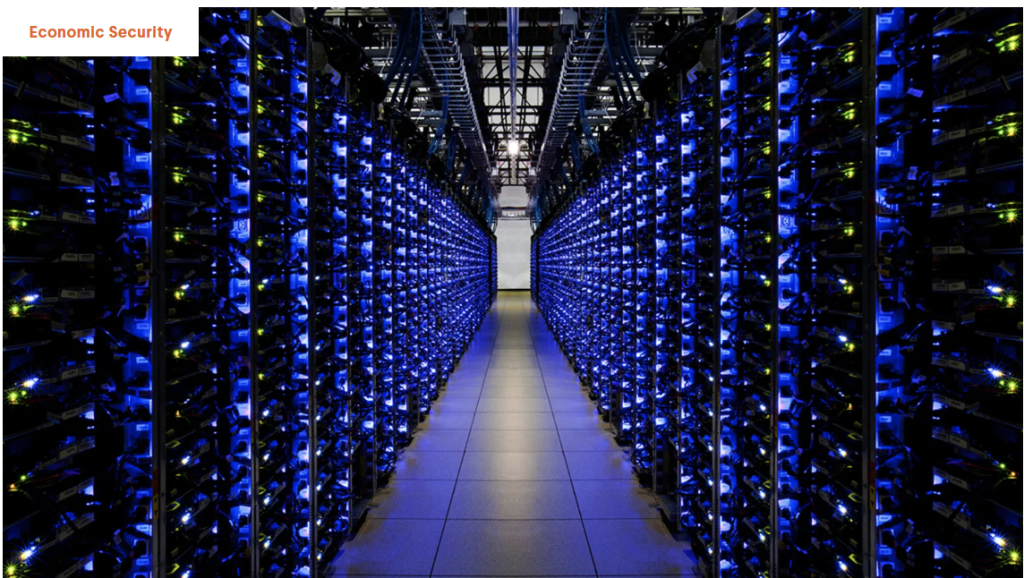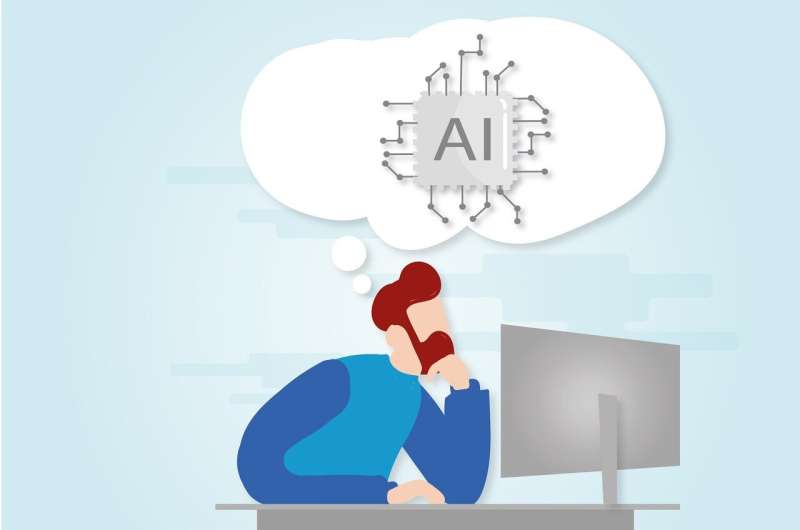稀土是目前大国竞争的焦点(共三篇)

稀土问题仍然是中美贸易谈判的主要障碍
根据近期的媒体报道,今年10月末中美在三大焦点问题(稀土、大豆和芬太尼)达成框架协议,进一步的贸易谈判在大豆和芬太尼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在稀土问题上仍然无法达成协议。
《美国之音》报道,尽管美国农业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大豆的采购速度远低于预期,美国农业部长表示仍有信心中国将履行承诺,完成今年1200万吨的采购指标。
根据白宫的公报,中方承诺在今年购买美国大豆1200万吨,明年增加到2500万吨。美国财长贝森特对此作了更加具体的说明,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贝森特于 2025 年10 月 30 日表示:“中国已同意在本季至 1 月采购约1200万吨 美国大豆,并在未来三年每年采购至少2500万吨。”
业内人士承认,这只是框架协议中的一个意向性的目标,中方也没有公开承认这一承诺。
《美国农政策新闻》指出,自中美领导人会晤后,至今只确认了两笔从美国采购大豆,合计约 332,000 公吨。有关人士指出,这是已经装船交货的数量,而框架协议中的1200万吨指的是购买(下单)的目标量。
“芬太尼”问题是中、美框架协议中的另一个焦点议题,美方希望中国管制“芬太尼”原材料(又称“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出口。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帕特尔于11月10日访问北京。他此次北京之行是继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韩国釜山的会晤之后(10 月底),美中双方在打击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与跨国犯罪合作达成共识后所出现的最新动作。帕特尔访问北京的消息并未得到美国或中国的官方宣布,因此是一次秘密访问。
据报道,帕特尔在访问北京期间,与中方讨论了有关芬太尼的执法问题。会谈的主题为遏制流入美国的芬太尼原料,同时讨论执法合作。
这次访问是 FBI 局长十多年来首次访华。帕特尔在白宫记者会上指出,他访中的唯一目的就是削断毒品集团制造芬太尼用的原料。他宣称,与中方达成协议:中方“完全指定并列入所有13 种用于制造 芬太尼 的前体化学物质”,并同意控制“7 家用于生产该致命药物的化学品公司”。他还表示,他非常看重此次访问带来的成果,称这是“历史性的第一次”这种级别的中方配合。
帕特尔的这次访华,凸显了美中在毒品控制,尤其是芬太尼链条上的一个新合作维度。长期以来,美方将中国列为向墨西哥或其它国家流出制造芬太尼原料的关键节点。此次中方控制措施的宣布表明中国在该议题上做出回应。
虽然美中在很多领域竞争激烈,但毒品原料的流通是一个相对“双方都能谈”的议题。中方有兴趣控制化学品出境,而美国则强调减少国内死亡与执法压力。此外,这次访问背景也有政治意味:在美中大环境高度紧张、科技与安全领域争端加剧的背景下,选择在毒品控制议题上取得成果,被视作一种“低争议、高收获”的外交路径。
但是中、美两国在稀土问题上的谈判却遭遇困难。
据美方媒体报道,目前美双方达成有关稀土及关键矿产出口管制的初步协议:中方同意暂停或放宽此前对稀土、镓(gallium)、锗(germanium)、石墨(graphite)、锑(antimony)等关键矿物的出口许可/管控要求,将“暂停一年”某些出口控制措施。
谈判团队被设定在2025年11月末敲定框架协议的细节。美国的短期目标是:避免中国在稀土、镓、锗、石墨等关键材料上实施突然性的实质断供,中期目标是通过谈判换取 12–24 个月的缓冲,以便争取时间,让美国及盟友建立“非中国供应链”。虽然还未完全解决结构性依赖问题,但至少在中、短期内市场风险有所缓解。此议题也引发欧洲、亚洲国家高度关注:例如德国财政部长访问北京,其日程中就包括稀土出口控制议题。
鉴于这一谈判进展缓慢,美方又开始露出威胁的态度。
美国财长贝森特称:“中国已经向全世界敲响警钟。他们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如果中国选择成为一个不可靠的伙伴,那么世界将不得不与之脱钩。”
11月16日,贝森特接受《福克斯新闻》晨间节目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希望在11月27日的感恩节之前,与中国敲定一份保障稀土供应的协议,协议生效后,稀土供应将“恢复到4月4日之前的自由流通状态”。
他还表示,倘若中方“变卦”,美国有多种报复手段。他还说:“特朗普总统威胁加征100%的额外关税,确实给了我们巨大的杠杆。”
《华尔街日报》近期的一篇报道点明,中方的震慑性举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稀土产业的复苏。然而,且不论重建西方稀土供应链本就需要时间,更何况该行业此前就已经经历过多次“虚假繁荣”。事实就是,中国以外的稀土行业,在经验和专业技术方面都存在缺口。(写于2025年11月17日)

西方国家稀土产业最难复制的“中国模式”
根据网上资料,稀土产业包括以下七个主要环节:
一、开采(Mining):从矿山开采稀土矿石,如包头白云鄂博、澳洲 Mt Weld、美国 Mountain Pass 等。
二、选矿/分离(Beneficiation / Separation):将矿石中的稀土富集,形成稀土精矿(rare earth concentrate)。
三、冶炼/深度分离(Refining / Separation into Oxides):将稀土精矿化学处理,分离成各种高纯度稀土氧化物(REO),如氧化钕、氧化镝、氧化铽等。
四、金属化(Metal Making):将氧化物还原为稀土金属(Nd metal, Dy metal, Sm metal等),用于制造磁体、合金、国防材料。
五、制造(Manufacturing):包括:永磁体(NdFeB、SmCo)、抛光材料、催化剂、合金材料、荧光粉、电池材料(La, Ce 系)等。
六、回收(Recycling):从废弃的电机、电子器材等中回收稀土金属。
七、取代/代替(Substitution / Alternatives):减少使用或不用稀土,例如:无重稀土永磁体,用铁基磁体替代 Dy/Tb 增强磁性能,用稀土含量更低的电机设计(如特斯拉 Model 3 的无稀土电机)
从环保的角度看,选矿/分离环节的污染最严重,占全链污染 70–80%。稀土分离需要上百次的“溶剂萃取”,大量使用盐酸、硝酸、草酸、有机萃取剂(磷酸酯类)和大量水资源。污染类型包括强酸废水、有机溶剂废液、放射性物质(铀、钍)。污染处理的高难度在于上百次循环,难以做到“零排放”,萃取剂极难完全回收,放射性沉淀物(尾渣)需要 300 年管理。
其次是金属化环节,污染也很严重,占全链污染的10-15%。这一环节涉及将氧化物还原为金属,主要方法包括钙热还原(Calciothermic reduction)、电解熔盐法。污染来源包括氯化物废渣、高温炉的粉尘、氢气/氯气泄漏风险等。
在稀土产业的污染中,最难处理的是放射性尾渣。稀土元素往往与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共生”:钍(Th,Thorium)和铀(U,Uranium),特别是在以下两类稀土矿中:(1)离子型稀土(南方稀土,江西赣南)含 少量钍,化学结合较弱,易被溶解出来;(2)混合型稀土 / 独居石(Monazite)含 较高钍、铀,国际上最典型。也就是说:稀土本身不放射,但稀土矿几乎一定夹带钍和铀。这两个元素在化学萃取过程中会被“洗出来”,形成放射性废物。
由于稀土产业的精炼和金属化是最污染、最危险、最难治理的环节,世界上多数国家愿意“开矿”但不愿“精炼”,因此全球稀土产业的重度污染大部分集中在中国。
在全球稀土产业链中,中国在以上第三和第四两个环节占绝对优势,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在过去 30 年确实承担了全球稀土产业链 80–90% 的污染,尤其是江西赣南、内蒙古包头、四川凉山等地区。
也就是说,中国建立稀土优势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高度污染为代价的。
1980-2010是中国稀土产业污染最严重的年代。根据网上资料,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大量私采 + 黑矿(尤其是赣南),山区被挖成蜂窝,酸浸液直接排入河流,废渣随处堆放,无防渗池、无尾矿库、无收集系统,大量放射性尾渣(含钍)无法管理,萃取车间无封闭 → 废酸直排。
中国从 2011 起全面“铁腕整治”稀土污染,2010–2015 是中国稀土治理的重大转折点。首先是“整治非法开采、清缴违法加工、取缔黑心冶炼。” 在此期间,最坚决的措施就是大量关闭非法矿山,同时开始建立世界最大规模的“防渗尾渣库”,包括:赣州稀土尾渣库群、包头白云鄂博稀土尾渣库,这些尾渣库是全球最大的放射性尾渣收容设施。
2016-2024,中国进入“绿色稀土”阶段,稀土产业整合为六大国企:《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中国五矿》、《广东稀土》、《厦门钨业》、《江西赣州稀土》, 统一环保标准,集中治理尾渣。采用离子型稀土全面改用“绿色浸取(生物淋洗)”,新方法包括生物浸矿(微生物)、有机弱酸、可控淋浸场(避免酸液乱流)等,将污染降低 80% 以上。在排放物处理方面,重稀土尾渣全部进入“集中监管区”,特别是钍系废物等全部,由政府统一管理、专库专储、实时辐射监测、禁止企业自行处置。
2022–2025:中国首次推动“零排放稀土”,包括:稀土废水零排放技术,稀土固废安全填埋 + 二次利用试验,数字化尾渣监测。
“包头稀土高新区” (全球最大的轻稀土分离中心)和“赣州稀土集团”(全球最重要的重稀土中心)是世界上最先通过“ISO14001 环保体系”认证的“全球最环保稀土企业”。
“ISO 14001” 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全球最权威的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它要求企业必须做到:1)系统化的环境管理(EMS);2)污染控制达标;3)废水、废气、废渣必须可追踪、可审核、可量化;4)持续改善(Continuous Improvement);5)必须通过第三方国际认证机构审核。
通过 ISO14001 就意味着企业的环境管理达到国际公认的标准级别,并且必须接受外部独立审核。
美国、日本厂商经多次参观后承认:“中国把稀土分离做到了世界最环保和最便宜。” 这也许是西方国家最难复制的“中国模式”。(写于2025年11月13日)

如何解决稀土供应链问题的“日本模式”
在探讨美国如何解决稀土供应链问题的同时,我们发现日本这个没有稀土资源的国家,却能很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稀土自主供应链。日本虽仍然在购买中国的稀土金属,但似乎并不依赖中国。
日本是如何解决稀土供应链问题的?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课题,即解决稀土供应链问题的“日本模式”。
如果说,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稀土供应链,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那么自从2010年因钓鱼岛事件引发中国用稀土制裁日本之后,日本政府为解决稀土供应链问题,已经有15年的历史。
在此长达15年的时间内,日本政府提出了清晰的战略构思和计划,拨款1000亿日元,建立了一个具有政府背景的专职机构 Japan Organization for Metals and Energy Security (JOGMEC-日本金属与能源安全组织),以“供应安全”与“制造业支撑”为导向,大规模投资稀土行业。
反过来说,也许正是因为中国卡了日本的脖子,才导致日本下决心进行了长期和不懈的努力,才走到了今天值得美国借鉴的这一步。
日本的教训提醒了所有国家和企业:稀土供应链的薄弱环节不仅在于“谁开矿”,更在于“谁提炼”、“谁加工”、“谁能回收”以及“谁能替代”。
其实,稀土并不稀缺,很多国家都有稀土资源,如今就连巴基斯坦也希望与美国合作来开发他们的稀土资源。也就是说,技术与加工能力才是关键。即便有矿但缺乏提炼和下游制造能力,仍可能落入“原料依赖”陷阱。
在2010-2020这10年内,日本建立了稀土矿物的多元化供应链,与澳大利亚、越南、印度、美国、欧盟合作,建立了“非中国稀土链”,包括通过JOGMEC直接投资日本国外的稀土矿山,例如澳大利亚Lynas Rare Earths Ltd(Mt Weld矿)和越南的 Đông Pao 矿(Lai Châu省)。
冶炼和分离方面,日本没有“直接控股”马来西亚工厂本体,而是通过 对 Lynas(母公司)的股权+贷款+独家代理与配额/优先权条款,把 Lynas Malaysia 的关键产能“绑定到日本市场”。这在法律/财务结构上是间接投资,在产业效果上等同于对马来西亚分离环节的稳定锁定,实际上成为日本控制的“海外精炼厂”,为日本提供绝大部分非中国来源稀土氧化物。
日本本身则集中在稀土氧化物的分离和精炼,例如住友金属、三菱、日立金属等,都具备成熟的金属冶炼、氢化、脱氧等技术,能提供高纯稀土金属。
在磁体与终端制造方面,日本具有制造高性能磁体的世界领先水平。日本在稀土永磁体(特别是 NdFeB / SmCo 等高性能磁体)制造方面拥有多家较为领先的企业,例如:
Shin‑Etsu Chemical Co., Ltd.(日本信越化学),其产品 “Nd Magnet N Series” 为高性能钕铁硼磁体,适用于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发电机、工业电机、家电电机等。
Hitachi Metals, Ltd.(日本日立金属),其产品范围包括 NdFeB 磁体、软铁氧体磁体、纳米晶合金等,服务于汽车、电子、可再生能源等应用领域。其制造能力加上研发能力,使其成为日本乃至全球磁体产业链中一个关键节点。
TDK Corporation(日本TDK),其在永磁体及磁性材料这一块亦具备相当能力。在汽车电机、工业电机、小型电子设备等领域,TDK 的磁体制造是其竞争优势之一。
Magna Co., Ltd.(日本玛格纳),专注于钕铁硼磁体、稀土磁体的生产与销售。其网站标注其产品种类包括 Nd-Fe-B/Sm-Co/Alnico 磁体。虽然规模可能小于
上述三家巨头,但在“专注磁体制造”这一细分中展示出日本中坚企业的范例。
日本虽然在矿石、分离/加工(上游)方面,依赖较多外部资源,但在下游“磁体制造”这一环节,是稀土材料最终转化为高增值部件的关键。日本的技术能力仍属世界前列,具备较完整能力:从高性能永磁材料(如 NdFeB)、到磁体成型、表面处理、组件制造都拥有领先企业。
日本在稀土回收(Recycling)与取代(Substitution)两方面的技术与体系建设,是全球最领先、体系最完整的国家之一。可以说,日本已经建立了一个“第二稀土矿山”——以城市废料回收为主、替代材料研发为辅,显著降低了对中国稀土的长期战略依赖。
日本在稀土“回收”方面的企业有很多家,例如Dowa Holdings(同和控股)、Hitachi Metals(日立金属)、Shin-Etsu Chemical(信越化学)、AIST(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等,它们从废弃的电机和电子器材中,每年回收获得的稀土约 4,000–5,000 吨,相当于其总需求的 15–20%。未来10年若回收体系全面扩展,可覆盖到惊人的 35–40% 国内消费量。
不能小看“回收”的能量。日本政府的“经济产业省”设有“关键矿物回收基金”,对回收企业提供税收减免与设备贷款,还制定了“家电回收法”、“汽车回收法”,规定制造商负责取回废弃产品,推行全国性“磁体回收计划”,资助 Hitachi、Dowa、信越等在全国设回收节点。
此外,日本还与泰国、印尼等国合作,将其电子废料回运日本提炼。日本已成为全球稀土再生中心之一。
在“取代”方面,日本“经济产业省”设立“稀土替代材料计划”(Rare Earth Substitution Program),2021–2030年预算约500亿日元。支持大学、研究所与企业联合攻关“无稀土磁体”、“高效催化材料”、“非稀土发光粉”,技术成果逐步产业化,部分进入汽车和家电产业链。例如,日本已经能够用取代减少对重稀土(Dy、Tb)的依赖,在新能源汽车电机用磁体中,Dy 含量已下降 70–90%,显著减少对中国重稀土的需求。
日本本岛没有稀土矿,但是日本属下南鸟岛附近的海底,却发现了丰富的海底稀土矿,日本计划于2026 年启动勘探/试采,建立“国内可控制”的稀土资源来源,从战略上减少外部依赖。
日本是否已经完全摆脱了对中国的稀土依赖?这个结论也许还言之过早,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说,日本是企图摆脱对中国依赖最成功的国家,也是目前对中国稀土依赖程度最低的国家。

作者
-

作者为北美知名时政评论人、本站特约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