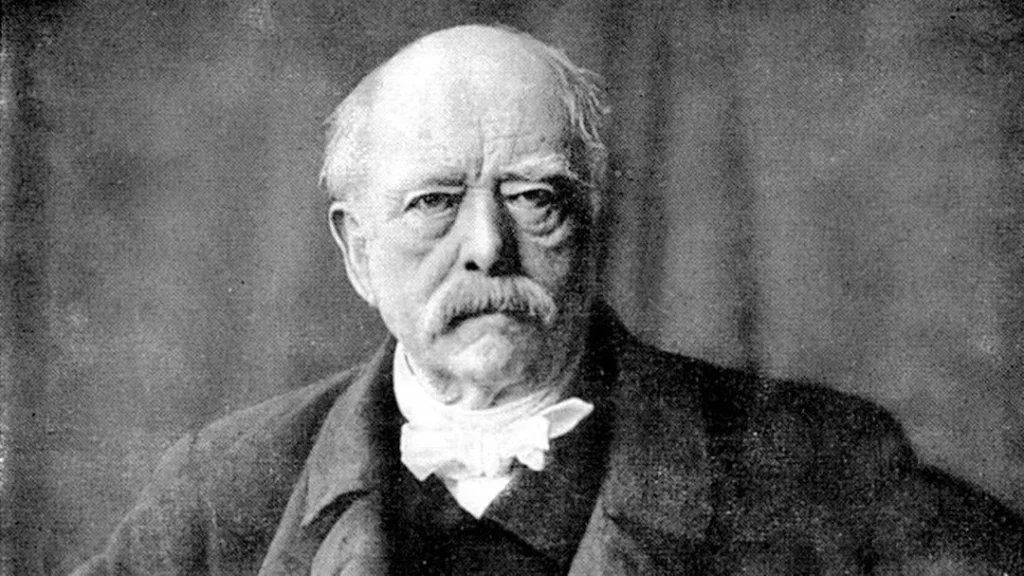布鲁金斯研究员:尼克松式重启是否可能?

【编者按:最近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可能计划秋季携带美国大公司的CEOs访问中国。学界一直在探讨特朗普在第二届任期内,是否会实现尼克松式的中美关系的再重启。今天,我们为读者翻译了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Patricia M. Kim 在今年2月分表的一篇文章,以帮助读者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在将来陆续发表对这个问题的其他看法。】
特朗普一直以“终极交易者”自居。他上任以来的行动——直接与习近平和普京接触,甚至提出冷战式的三边核军备协议——都凸显了他偏爱与强人进行幕后谈判。
关于特朗普可能与习近平达成何种“大交易”的猜测越来越多。特朗普会寻求像尼克松那样与北京实现关系重启吗?他会忽视中国对台湾的“侵略”,以换取北京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并帮助美国再工业化吗?他会因中国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而牺牲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吗?
北京方面也一直在试探。自去年11月以来,中国代表团络绎不绝地访问华盛顿,悄悄探寻可能达成何种协议。与此同时,在特朗普的圈子和美国外交政策圈内,对于华盛顿应该向中国提出什么要求并没有达成共识。一些人认为,重新平衡美中经济关系应是优先事项。另一些人则坚称,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是徒劳的,主张全面战略脱钩。
然而,尽管猜测众多,但没有人能描绘出“大交易”的完美轮廓。原因很简单: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交易。
达成单一、全面协议的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它可以在动荡、高风险的关系中带来清晰。但历史证明,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自尼克松1972年戏剧性访华以来,美中关系的管理并非依靠宏大的姿态或追逐某种神秘的最终状态,而是需要艰难而持续的战略管理工作——平衡竞争与合作,设定明确的界限,并不断重新校准以保护美国利益。
“单一突破”的神话
几十年来,美国和中国都一直在寻求一种难以捉摸的、包罗万象的协议——一种能一举解决双方根本性争议的协议。然而,双方屡屡失望。现实是,它们的许多核心诉求是不可调和的。
对中国而言,“大交易”将意味着确保美国默认其核心诉求:吞并台湾,认可中共在国内的统治,以及在亚洲及其他地区拥有无可争议的势力范围。中国还希望在保持自身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不受限制地进入美国市场和技术。中国将美国的任何反击都描绘成限制中国崛起、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尽管其自身在国家主导的经济干预和强制性贸易行为方面劣迹斑斑。
对美国而言,“大交易”将要求中国拒绝其不愿让步的核心内容:放弃对台湾以及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侵略”,遏制长期以来损害美国企业利益的非市场经济政策,改善其人权记录,并在国内接受民主实践。华盛顿长期以来还寻求北京帮助向朝鲜(如越南战争时的北越,或今天的朝鲜和俄罗斯)等“流氓国家”施压,但这些方式将危及中国与其少数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使其在战略上陷入孤立。
这些要求触及了每个国家核心战略利益、政治认同和价值观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全面协议的尝试都失败了。
也许特朗普是北京能遇到的最佳谈判伙伴,鉴于他对台湾的非传统看法——他更多地将台湾视为经济竞争对手而非关键民主盟友。但即使在他自己的政府内部,更不用说更广泛的共和党内,也鲜少有人同意这种观点。北京也深知,任何一任美国总统所做的承诺都可能被下一任总统重新解读或推翻。中国长期以来的抱怨是,尽管过去有《三个联合公报》和其他美国的再保证,华盛顿却改变了其“一个中国”政策的条款。
更重要的是,中国也是如此。尽管其是威权体制,习近平也不受任期限制,但北京一再表明,只要符合其利益,就会违背承诺。习近平2015年在白宫承诺不将南海岛屿军事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一种更现实的方法
真正有效的方法并非是宣告双边接触是徒劳的——而是任何方法都必须立足于现实,而非一厢情愿。美中两国不应追逐难以捉摸的“大交易”,而应采取一种更务实、更自律的方法。
这可以从特朗普和习近平建立广泛的预期开始——勾勒出双方各自寻求什么(例如稳定公平的经济关系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相互保障)以及他们拒绝什么(战争和全面脱钩)。
从那里开始,艰苦的工作才正式开始:就贸易、芬太尼、军备控制和危机管理等问题谈判有针对性的、具体议题的协议。
同样重要的是建立可信的执法机制,以处理违规行为并确保问责。华盛顿必须准备好应对违规行为,惩罚不当行为,并战略性地部署激励措施以鼓励遵守。
华盛顿如果希望塑造有利于自身的美中关系,必须从实力出发与北京打交道。这意味着投资于自身的经济韧性、军事能力、技术领先地位和全球联盟。同时,美国应保持与中国的适度经济和外交联系——这不是一种让步,而是为了自身利益。如果没有这种接触,美国影响北京的能力就会减弱,从而使军事对抗成为唯一的杠杆工具——这种结果既危险又不切实际。
几十年来美中关系一直都是这样管理的。这从来都不容易,也常常不尽如人意。但归根结底,这种方法比任何极端——无论是天真的绥靖还是彻底的敌意和脱离接触——都能带来更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