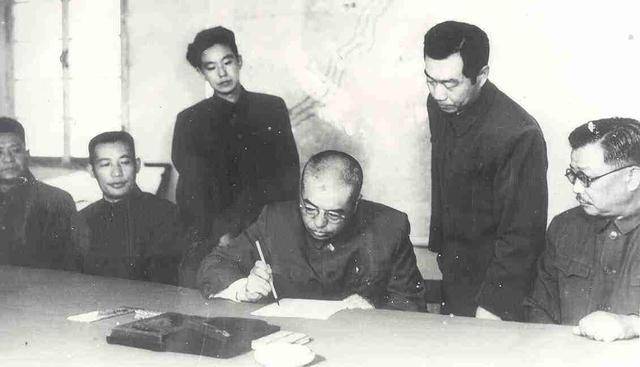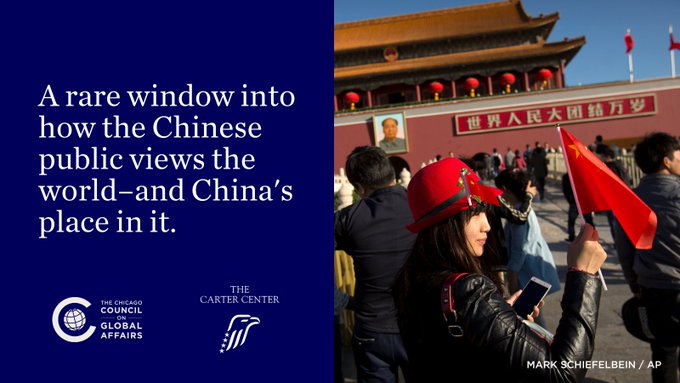中国学者激辩中国在俄乌和平进程中可扮演的角色
- 分析
- ZHANG Juan
- 18/08/2025
- 0

这两天全世界都在聚焦的美国就乌克兰问题而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等各方的紧张角力中,中国在这当中是沉默的。
这当然也不奇怪,因为中国不是交战双方的直接参与者。 不过,位于北京的全球化智库的创始人王辉耀和《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两位在中国媒体生态中非常活跃的媒体评论人士均对此发表了看法,认为中国还是可以在俄乌和平进程中发挥一定作用的。
中国官方的态度一直是支持俄乌双方尽早结束战争。北京时间周一,在特朗普和普京阿拉斯加会议之后、在乌克兰和欧洲与特朗普举行白宫会谈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了中国支持乌克兰和平的立场。她说,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乐见俄美双方保持接触、改善彼此关系,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
在交战三年多的时间里,西方一直指责北京与俄罗斯保持生意往来,尤其是对俄罗斯石油的购买延续了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战斗力。而对于北京来说,中国不仅和俄罗斯保持生意往来,还是乌克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不存在偏袒一方的说法。
在即将到来的俄乌和平进程中,中国希望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在下文中为读者摘录了三篇来自中国学者和媒体评论人士就该问题的分析。他们分别是胡锡进、王辉耀和清华大学的达巍教授。他们就俄乌进程中中国可能发挥的影响或者作用进行了阐述。在这三人的描述中,胡锡进主要是从中国支持和平进程这个立场对谈判的正面影响来阐述,而达巍则认为中国不可能扮演核心的角色,只能是参与的角色。不过,王辉耀则憧憬了中国在未来乌克兰安全保障中所扮演的实质性角色。
胡锡进在其文章中写道,“中国是乌克兰和平进程隐形而强大的存在,中国是否支持美国调解俄乌冲突,是否支持、配合和平进程,结果将截然不同。” 以下为他的分析:
首先,中国公开表示,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乐见俄美双方保持接触,改善彼此关系,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进程。而且,中国的这个真实态度非常重要。中国没有在结束俄乌冲突上坏特朗普的事,这是因为结束这场冲突对中国有利。它可以让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进一步放开来做,停战后,中国再向俄罗斯出口军用设备,西方就不再有理由反对了。另外,中欧关系将消除了一大麻烦,欧洲一直声称中国对俄出口“军民两用产品”,声称中国在帮助俄罗斯维持战争,质疑中国的中立路线。
特朗普推动普京结束战争,除了满足俄罗斯围绕领土和战后安排的基本要求,还以加强对俄制裁,尤其是对俄石油征收“次级关税”作为最大的施压杠杆。而如果对购买俄罗斯石油施加“次级关税”,除了印度已经被以此为由提高关税外,中国将首当其冲。在石油问题上,中俄美形成了一个压力循环三角,中国配合实现和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中国准备跟美国杠,并向俄罗斯发出信号,普京就可能更加强硬,对特朗普提更多要求。
中国与美国就关税开战,已经打了一大轮,关税休兵不仅有利中国,对美方同样重要。从根本上说,中国不怕与美国再打一轮。现在印度因为购买俄罗斯石油被美国加征了关税,但特朗普15日表示,他暂时不会考虑因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对中国加征关税,同时补充说,他“不得不在两三周后考虑这个问题”。特朗普在中国买俄罗斯石油事情上的微妙表态是中美俄“压力转换三角”绝版模式的一部分。
中国没有就“次级关税”做出我们会具体怎么做的倾向性表态,官方舆论很少将它与中国联系起来,这个态度各方肯定没少玩味。我认为,加上中国对愿意看到俄乌冲突平息的表态,它对俄美尽量拿出一个可行可落地的和平方案是一种鼓励,因为和平进程如果失败了,中国将怎么做是不确定的。
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8月13日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发表文章《 中国可以帮助特朗普与普京结束乌克兰战争》。他认为,若在北京召开七方(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乌克兰及欧盟)会谈,有望推动联合国支持的维和部队部署,从而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他在开篇写道,“实现真正的和平不仅需要美俄双方的参与,还需要乌克兰、欧洲、联合国以及中国的共同努力。” 他写道:
中国可召集后续峰会,汇聚乌克兰、俄罗斯、美国及欧洲各方领导人,实现面对面磋商。目标是建立一个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乌克兰及欧盟代表组成的正式七方会谈框架。中国不仅在外交上具备重要影响力,在经济上也拥有关键杠杆作用。2023年,中国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最大贸易伙伴,贸易额分别达到2401亿美元和128亿美元。两国皆为“一带一路”倡议成员,中国对乌克兰粮食出口的稳定性尤为关切。因此,中国可以为俄罗斯提供缓冲渠道,同时为乌克兰提供重建与恢复援助。
一旦有限停火实现,联合国维和力量便可在此基础上展开行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布鲁塞尔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将美军部署至乌克兰不可接受,“任何安全保障都必须由具备实力的欧洲和非欧洲部队来支持”。
赫格塞思的意见提供了可行路径。一支有效的维和力量可由非结盟国家与欧洲国家混合组成,形成政治上可行的中间方案,缓解双方担忧。其实际存在将抑制未来冲突,并启动重建进程。该部队可由德国、法国、英国、波兰、意大利五个欧洲国家与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埃及五个金砖国家组成。这种安排既凸显中立性,又分担责任,确保广泛合法性与持久安全保障。
金砖国家与欧洲安全事务的相对疏离可转化为优势。由于历史纠葛较少,它们更能够提供各方可接受的创造性保障和信心建设措施,包括维和支持及长期发展援助。
战后重建计划至关重要。乌克兰重建任务需要持续的国际努力,不仅包括资金,还需物流与技术支持。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具备工程技术和融资能力,可助力重建。中国的参与不仅能够加速乌克兰复苏,也展示了中国对和平、稳定与包容性发展的广泛承诺。在此框架下,可成立小型工作组处理具体问题:人道援助、领土争议、能源基础设施及长期安全保障,并由多方参与强化落实。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巍在7月29日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析。他在文中也提到了中国在可能的和平谈判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即不可能是核心角色但有可能是参与的角色。他写道:
理论上,中国很有能力促使各方坐到谈判桌前。中国近年来在调解国际冲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包括促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而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将消除改善中欧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这样的突破还可以推动国际秩序走向更大的多极化,并抵制中俄一方与美西方国家另一方之间日益固化的二元对立。如果中国能够成功结束战争,将提升其作为负责任世界大国的国际形象。
然而,现实情况是,中国不太可能在解决冲突中发挥核心作用。它所能发挥的任何作用,最多也只是次要的,仅限于参与。如果多边和平进程得以形成,中国若受邀将欣然入席。但俄罗斯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当事方,美国和欧洲则通过军事援助间接参与。如果两个主要交战方——俄罗斯和乌克兰——不愿意停止战斗,并且双方都对战后停火安全保障保持警惕,那么中国作为第三方调解人将不会成功。
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也限制了其有效调解冲突的能力。中国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限制了其回旋余地,因为北京不愿向莫斯科施压以做出重大让步。中国的战略文化塑造了其外交:当一个国家与中国大体上保持一致时,北京不愿批评该国的具体政策——即使私下里存在分歧。西方国家一再敦促中国利用其影响力向其他国家施压——包括伊朗、朝鲜、苏丹以及俄罗斯——但中国通常会拒绝这些呼吁。
同时,中国与美国和欧洲的紧张关系进一步限制了其作为调解人的潜在效力。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可能不希望看到中国主导和平谈判,即使中国愿意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会推动对俄罗斯有利的解决方案。如果其他各方结束战争,中国领导人则希望为维和与战后重建工作做出贡献。但中国不太可能首先主动促使各方坐到谈判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