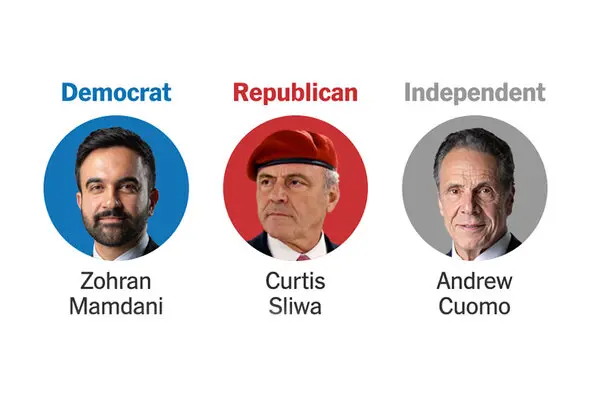中国人选美国总统为何比美国人更准确?
作者:那小兵 来源:凤凰博报作者博客
金哲朗:最近有位美国在华留学生搞了一项有趣的调查,他让中国读者虚拟投票选举美国总统,结果发现中国人普遍喜欢川普和希拉里,而且发现中国人大多是“中间派偏左”,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那小兵:这的确很有趣,我本来也想过搞同个问卷调查,但好像凤凰网已经有类似的了,所以没有搞。后来读到另个网友的相关文章,让我对这个问题格外感兴趣了。虽然这个统计数量只有2千多人,但毕竟是个比较好的开始。不过,我认为这个统计设计本身有一些问题,主要是概念不清晰,导致调查结果相关性减弱,说服力还不够充足。比如,他把“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两个对立坐标,大家对这两个概念理解不一样,或者说太敏感,这影响到了调查真实性。另外,他还用了“自由”和“保守”两个概念做对应坐标,中国人对这两个概念很陌生,而且有自己的语境和文化背景,很难理解,也影响到了调查准确性。如果我做同类调查,会着重对具体政策的态度和看法入手,而不是从抽象政治概念切入。
不过,我还是从中观察到一些有意义的趋势。中国人如果投票选美国总统,两国民众竟然不约而同选出同两个候选人对决,这说明中国人已经懂得如何着眼考虑美国人所关切的问题做选择,这间接表明中国人已经逐步明白和适应民主选举文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读者非常清晰地把台湾和美国选举分别开了,对于台湾选举他们投射了更多的个人感情色彩,而对于美国选举反而非常理性。我个人认为,中国和美国都是大国,两个国家的百姓都具有一定的“大国统一观念”,美国人用“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美国主义)解读这种心理,而中国人这个心理更多来自固有的“天下归一”政治文化传统,大家需要祖国统一,民族统一,大家有话好好谈,大家都需要稳定发展,这在两个大国都很有市场。你如果去欧洲看选举就不同了,比如,意大利人投票参与比率最高,民粹情绪也最烈,甚至还夹杂一些分裂主义情绪。美国投票比率远比欧洲低,也低于台湾和其他亚洲地区,反而更突显了大国民主模式,这就是所谓的“代议制信任度”很高造成的。
从这份统计看,如果中国人搞一次虚拟总统选举,得票最多的很可能就是现任领导人,甚至得票比率远高于任何一位美国竞选人。我观察到,超过85%的中国参与者都集中在“中间派偏左”的坐标位置上,其实这些被调查者是把美国选举当成一面镜子,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向,这就是说,他们不希望对现有政治格局有大的改变,但同时希望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度。我个人的观察也可以证明这点。我最近发表的《中国历代体制改革失败的教训》也得到了类似的读者反馈,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包含着浓厚的“维稳”元素,不像美国人那么看重个人自由,而是更多关注“集体共识”这个东西。在中国人看来,不论你打出什么党派旗号,最重要的是维护安定,不论你个人如何创新概念,都要被纳入集体观念中。
我们从大中华其他地区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比如,香港打伞运动最后无疾而终就是个例子,激进学生出来表达的主题得到不少人认同,但一涉及到香港安定社会环境话题,学生的支持者很快变成了沉默者或反对者。甚至连台湾的葵花运动也有类似情况,当那些学生非法进入立法院后,原本跟着叫嚣的公众反而沉默了,起哄的声音大大减弱,只剩下蔡英文那些吹鼓手在嚷嚷,反而弄巧成拙。这让我想起当年清末时期的宪政运动,无论是保皇派和革命派都希望和平达成国家统一共识,不巧却被激进派武昌起义打乱了进程,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真正破坏民主的不是保皇派,而是激进派,因为保皇派也得遵守共识规矩,最后也会妥协,但激进派只会捣乱,就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法国大革命民粹派那样胡闹。文革动乱也有这种深刻教训。恰恰美国民主体制也是非常排斥所谓“第三党派”的,因为这样才便于如此巨大的国家达成共识,否则会变成民粹式国家分裂。最近,埃及“颜色革命领袖”出来自我检讨失败原因,说:“社交网络不但没有增进民主,反而形成了民粹派性内斗,最终导致埃及社会瓦解的悲剧”,可见激进主义非常危险,我认为他的检讨是真诚的。
我还是那个观点,中国改革要注重文化更新,注重思维方式的更新,要培养新的国民情感方式,要培养民众理性思维心理,不要盲动搞体制革命,体制改革应当是渐进性的改良,而不是颠覆性的,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稳定进入民主文化社会。
来源时间:2016/2/10 发布时间:2016/2/10
旧文章ID:8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