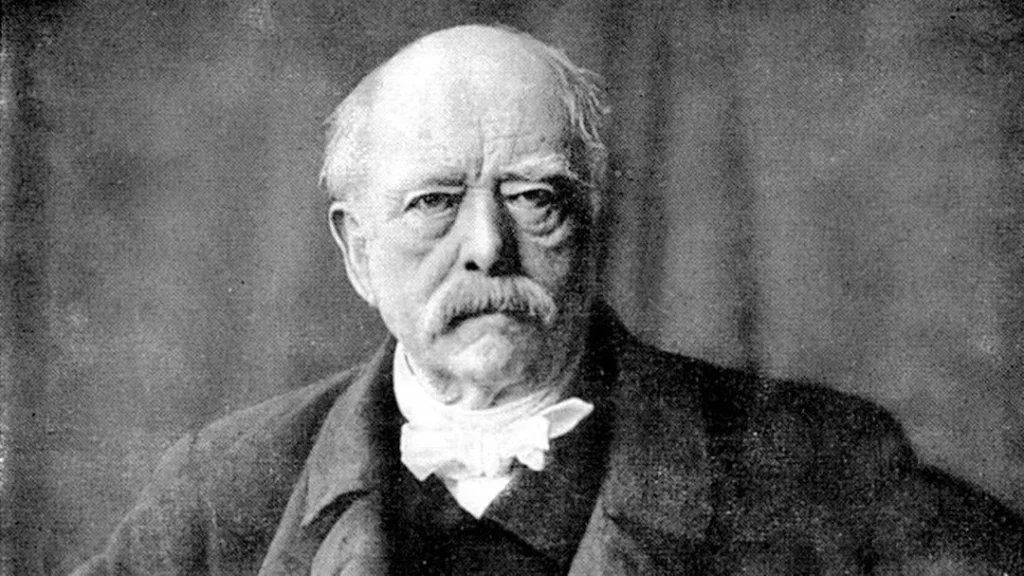美前副国务卿坎贝尔 :中美危机一触即发

作者:库尔特·M·坎贝尔 (原文刊发在2025年10月6日《外交事务》,坎贝尔曾经担任拜登政府的副国务卿,以及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
2023年10月24日,一架美国空军B-52轰炸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国际空域执行夜间任务时,被一架中国战斗机拦截。中国飞行员在一系列危险的高速机动中,将战机飞到距离美机仅十英尺处,令两架飞机及机组人员都陷入险境。这一事件发生在2023年6月之后不久,当时美国海军驱逐舰“钟云号”(USS Chung-Hoon)正通过台湾海峡,一艘中国军舰高速从其左舷超越,随后突然转向,从“钟云号”舰首前方约150码处横切而过,迫使美舰急速减速以避免相撞。中国军舰无视美方多次尝试进行的舰对舰通讯,违反了公海近距离接触的标准作业程序。
这些只是近年来中美军方之间众多“擦枪走火”事件中的两例。尽管美国的军事战略家和规划者越来越专注于应对中国在西太平洋,尤其是台湾问题上可能采取的有意军事行动,但这些近距离险情却令美国分析人士深感忧虑——担心一次意外或误判就可能将中美两国卷入一场双方都不想要的冲突。
这种担忧并非新鲜事。数十年来,美国一直试图为中美军事关系设置“护栏”,常常借鉴冷战时期维持美苏关系稳定的经验。在1990年代,当时华盛顿仍对北京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美国战略家强调“安抚性”措施,例如军事对话和沟通机制。而如今,随着中国军力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存在不断增强,中美从贸易到科技的紧张关系持续升温,美国官员更强调建立“信任措施”——以提升军事行动的可预见性,并确保在危机中沟通畅通,从而避免小事件演变为全面冲突。
“如今,中国是世界上军力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时也是核力量增长最快的国家;美国则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美国众议员亚当·史密斯上月访问北京时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就各自的能力与意图保持定期沟通是极其危险的。”
然而,尽管美方多次尝试推动加强军事交流,中国方面仍拒绝建立甚至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北京之所以态度冷淡的原因虽然随着时间演变,但始终如一的是:对美方主导倡议是否符合中国利益抱持深刻怀疑。华盛顿要想克服这种长期存在的不信任并非易事。但如今,随着中美军力被普遍认为趋于接近,潜在升级的风险也在上升,美国官员若希望重新推动中美军事外交,就必须理解这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并尽其所能设法化解。
苏联的模式
冷战时期的美苏军事外交,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竞争对手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成功范本。尽管美国与苏联是生死攸关的核对手,但在冷战后期,两国军方仍建立了相当程度的军事接触。1972年签署的《海上防止事故协定》(Incidents at Sea Agreement)旨在防止舰艇碰撞,降低海上意外升级的风险;1989年的《防止危险军事事件协定》(Prevention of Dangerous Military Incidents Agreement)则限制某些武器的使用,例如可能因鲁莽照射而导致失明的激光武器。
这些协议虽非万能,但确实在防止危机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期间,美苏部队仍发生过多次危险而惊险的遭遇,但这些沟通机制帮助双方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当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外交关系时,美国战略家尝试将类似的模式运用于与中国军方的关系。那时,双方的军事接触和交流还较为有限,例如就军事理论和一般训练进行会议。然而,这些努力在1989年骤然中断——华盛顿因北京对天安门广场抗议者的军事镇压而暂停所有军事交流。
进入1990年代初,中美军事关系略有恢复,但未能缓解不断升高的紧张局势。两国军队在同一地区活动的频率日益增加,引发了一系列危险的接近事件。比如1994年10月的黄海事件,一艘中国潜艇和多架战机在美国第七舰队,包括航母“凯蒂霍克号”(USS Kitty Hawk)周边危险地巡逻。当时,中国高级文职与军方官员一再向华盛顿抱怨,美国侦察机飞得过于接近中国领空——这种说法并非完全错误,因为这些飞行确实旨在探测中国的防空系统与作战程序。
1995年至1996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将这些问题推向高潮。面对中国在台湾周边海域的炮击行动,美国向西太平洋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以此展示武力、遏制解放军进一步挑衅。然而,中国方面认为这一举动极具羞辱性且具有升级性质,从而加深了双方军方之间的不信任。
在华盛顿,第三次台海危机带来的紧张局势促成了两党共识,即有必要与北京建立军事沟通机制。而五角大楼的美国文职和军方领导人推动改善与中国军方关系,也出于其他考量——解放军长期在中国国内政治体系中扮演重要的官僚角色,并随着21世纪临近,其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强。因而,与解放军高层建立关系不仅有助于防止灾难性冲突,也被视为影响北京战略思维与国际行为的一种方式。
1996年至1999年是美中建立军事沟通的高峰期。双方相继推出了《1998年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Military Maritime Agreement),以防止海上危险互动,并建立了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高层热线。这两项举措在1998年江泽民主席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峰会上被公开肯定。此后,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军官开始与中方对口官员举行会谈,讨论双方军事理论,以避免将常规部署与训练误判为敌对行动的准备。双方甚至进行过短暂的核领域交流,包括核弹头安全与指挥及发射程序等议题。
然而,这种接触的深度仍然有限。双方在这些沟通机制的用途和意义上存在根本分歧。中国尤其不愿让军方过于“透明”,因为当时中美军力仍存在明显差距。冷战结束后,美国潜艇与侦察机更频繁、几乎不受限制地在中国大陆沿岸及南中国海执行任务。中国战略家将重点放在缩小这种能力差距上,并普遍认为美国推动信任建立措施并非真心防止意外冲突,而是出于监控和约束中国军力的算计。依照这种看法,正式的信任机制不仅可能在危机中为美国所用,也会在长期内成为华盛顿限制解放军扩张的渠道。
中国官员仍维持有限的与美军联系,但更多是为了自身目的——例如限制美方在中国近海地区的军事部署与侦察行动。北京刻意使军事交流和承诺保持模糊、谨慎且程式化。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增强互信,反而加剧了美方操作人员的焦虑与不确定感。
这一问题在2001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年,中国战机与一架美国EP-3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相撞。美机被迫在驻有中国军方基地的海南岛紧急降落,机上24名美军人员被中方拘留。美方试图启用高层沟通机制,却得到的只有沉默与推诿。电话无人接听,美方人员被关押在军方设施中接受48小时审讯(随后被扣留共11天后才获释)。
偏好不透明
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及其活动的忧虑与日俱增。然而,北京方面却变得愈发不愿公开透明。美国多次尝试建立各种机制,以防止、管控或遏制在多个军事领域中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从网络空间到外层空间——但这些努力几乎都遭到中方的误导或直接拒绝。即便中美之间启动了与安全相关的对话,也未能达到哪怕是有限的预期。例如,奥巴马政府时期设立的网络安全对话,未能有效限制中国的网络入侵行为。而且,这类互动往往激起更多的怀疑与不信任,而非增强信心。比如,当美军在得克萨斯州胡德堡(Fort Hood)邀请中方军官观摩装甲部队训练时,一位中国来访军官事后将简报与演示描述为“带有威胁性、意在震慑”的行动。
中国的这种克制与拒绝,源于其根深蒂固的猜疑心理,但具体表现方式多样。北京长期担心,与华盛顿签订双边协议将意味着“永久性地确认中国的军事劣势地位”。从这种视角看,中美间的军事行为准则只会成为美国的“免责卡”——允许美军继续在相关地区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因为美国可以通过风险管理与危机脱身机制避免严重后果。中国军方普遍认为,这类“信任建立措施”利益不对称——透明度对华盛顿更有利,而对北京则构成不利。
历史上,中国之所以不愿参与此类信任机制,还因为这些机制往往以美苏模式为蓝本。这并非出于对其实效性的质疑,而是担心其象征意义——中国战略家深知,这可能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美国应将中国视为类似苏联的军事对手。这与中国在2000年代初期的更广泛外交宣传是一致的——当时北京努力淡化“中国崛起”的说法,转而强调“中国发展”的概念。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态度如今已有所改变:北京现在希望被视为一种“超级大国”。但与昔日的苏联不同,中国似乎并不担心与美军关系恶化所带来的升级风险。相反,北京似乎认为这种风险对自身有利。华盛顿通常倾向于公开展示其军事实力,以期以“威慑”让对手保持克制;而北京则倾向于在军事部署、外交互动与战略原则上制造不确定性,希望借此增加美军在近距离行动时的焦虑与顾虑。这种策略的本质是政治性的。虽然有部分中国学者,甚至一些解放军军官主张加强中美军事透明度,但中共中央领导层整体上更偏好保持对解放军现有能力与危机应对机制的模糊。最终,中共认为,战略上的模糊性既能在危机中最大化灵活度,又能增强威慑力。
而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党说了算。解放军是党的武装力量,而不仅仅是国家的军队。中共主导的军队体系在危机中严密把控决策权,并视各种“信任建立机制”为潜在威胁——可能削弱党的控制权和权威。某种意义上,这几乎是“制度性设计”:军事外交在危机情况下势必干扰中共的集中指挥——而这恰恰是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最不容松动的时刻。
有可能,中国高层领导人正在淡化甚至忽视“意外战争”的风险。毕竟,自朝鲜战争后期以来,中美之间并未经历严重的军事紧张。而或许,只有当这样的紧张真正发生时,北京才会改变立场——正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莫斯科与华盛顿才建立起明确的军事沟通机制一样。
但美国仍应继续努力,在危机发生之前建立稳固的危机沟通渠道。尽管这些努力可能最终未必成功,但面对可能相互对峙的庞大军事实力,21世纪的两个超级大国必须具备足够的远见,在印太地区爆发“古巴导弹式危机”之前,就先建立起这样的沟通机制。
作者
-

卡贝尔(Kurt Campbell)是美国外交官、学者和企业家,他在拜登总统任期出任国安会印台事务协调员和副国务卿,他还创立了咨询公司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