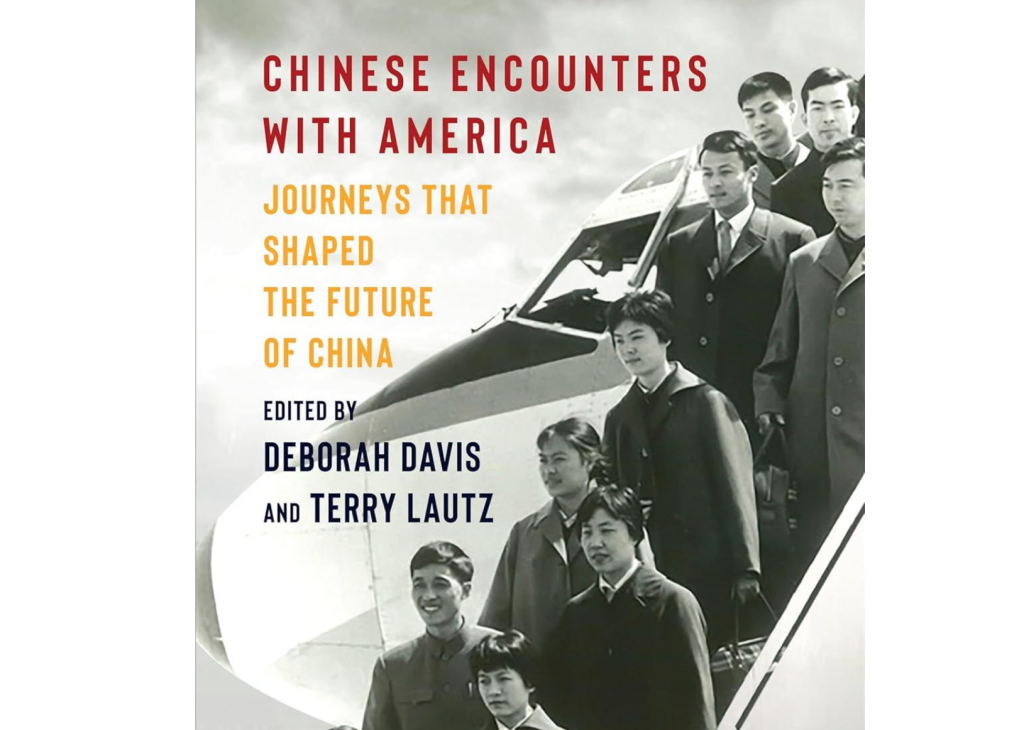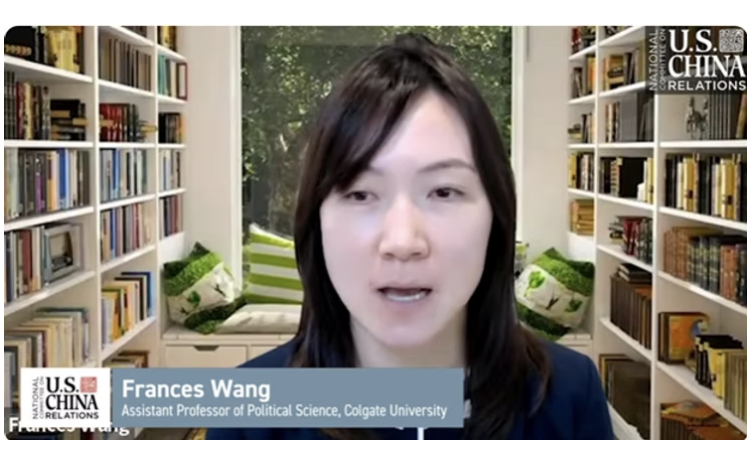专访柯庆生:美中关系如何从利益攸关走到战略竞争

编者按:本文是CSIS安德鲁·施瓦茨采访柯庆生教授的播客,该播客2025年6月3日上线,题目是“美中竞争的终极是什么”(What is the End Point of U.S.-China Competition?),由卡特中心实习生陈冠一翻译。
主持人: 我是安德鲁·施瓦茨(Andrew Schwartz)。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制作的播客节目《事实真相》(the Truth of the Matter)。我们在节目上讨论当今最重要的政策议题,与最能帮助我们了解时事的专家对话。为了探讨美中战略竞争的真相,我们邀请到了了CSIS的最新成员,地缘和外交政策研究部普利兹克主任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Pritzker Chair, Geo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Department)。柯博士曾是小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同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的公共与国际事务教授,以及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主任。柯博士,欢迎加入CSIS,我们很高兴有你加入。
柯庆生:感谢你的邀请,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主持人:您曾在小布什政府工作,是当时制定对华政策的官员之一。你参与了美国政府将美中关系定义为”利益攸关者”的战略(Responsible Stakeholder Strategy)的制定。我们现在距离那个定义有多远?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战略竞争,而不是利益攸关方了吧?
柯庆生: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利益攸关方”作为一项战略被广泛误解了。这个概念来自原副国务卿罗伯特·泽利克(Robert Zoellick)2005年的一次演讲。我认为人们误读了那次演讲,或者说他们忘记了演讲的内容,因此他们认为那次演讲是对定义美中关系的一次努力,其实它只是一种愿景,是说如果中国愿意的话它可以在双边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我不认为我们天真地认为中国会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但我们认为邀请中国扮演这个角色是有用的,因为中国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克林顿政府已经邀请中国融入国际经济和当时的多边国际机构。
我们当时的看法是,中国没有尽其所能维护它从中受益的国际秩序。所以,我们邀请中国扮演更具建设性和积极主动的角色,而这一战略的某些部分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成效,但它被看作是对美中关系的一种天真的描述是不确切的,不能把它与战略竞争相提并论。我认为这种对比并不公平,因为当时的战略就有竞争的元素。我们已经处于战略竞争之中,但却没有谈论它,也没有这样称呼它。我们没有在与中国人的每次会议结束时都提到它,因为我们不认为这是我们外交中必要的形式。但是你看,大部分与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相关的防务事务实际上是和那次演讲同时开始的,尤其是在军事领域。在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领导下,美国将更大比例的海军和空军资产转移到了亚太战区,以此应对中国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现代化。
另一方面,我们当时和台湾签署了强有力的军售协议,甚至在布什政府第二任期批评台湾领导人期间也没有停止对台军售。在我们批评台湾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我们认为是破坏台海稳定的举措时,我们仍然给他们提供相对长线的武器装备。我们看到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走向,我们认真地对待了它,但是没有把美中的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我认为不这样定义是有原因的。我确实相信我们处于战略竞争中。我认为,从分析的角度这样描述是可以的,但如果这是一场竞争,而且是纯粹的战略竞争,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想得到什么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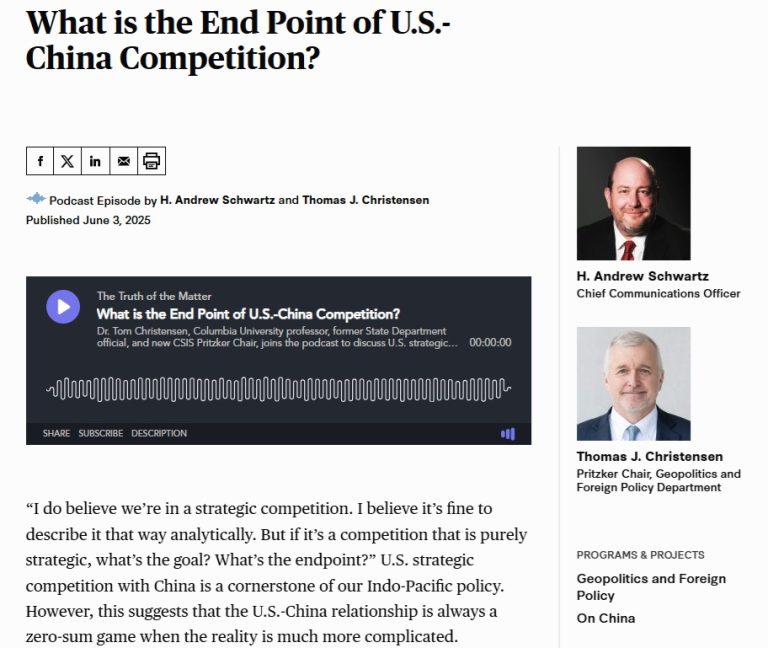
主持人: 我觉得称中美目前的关系为纯粹的战略竞争挺准确的。
柯庆生: 应该是准确的。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定了目标。它们不是描述性的,而是愿景性的。但现在如果我们只是说我们处于战略竞争中,我会有点担心,因为那样我们很容易走到一个零和博弈的立场,即任何对中国有利的事情对美国都是有害的,反之亦然。我认为我们的关系即使在今天也比零和博弈要复杂得多。
主持人: 那么请你告诉我,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这一战略竞争?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没有思考和讨论到的?
柯庆生: 我们有在讨论这个战略的终极目标,但是我们是否有在最大限度地高效执行这个战略是另一回事。我们几十年来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我们一直紧密交往的盟国和友邦的关系。我们在该地区里里外外有超过60个盟国和友邦,我们与这些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互相呼应。这是我们相对于中国的巨大优势。我担心的是,我们并不总能以最好的方式管理与这些盟国和友邦的关系,也因此不能有效地利用这个优势对抗中国。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新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可能会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损害我们与盟国和友邦的关系。我知道新政府说它们在关注(美中)战略竞争。它们表示(在与中国竞争时)与盟国和友邦的关系很重要,我对此感到深受鼓舞。
在感到鼓舞的同时,我也担心(新政府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削弱盟国和友邦对美国的支持,这可能使我们更难执行我们的竞争战略。在军事方面,美国战略有一个方面在过去几届政府中一直在变化,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政府,(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国在东亚需要展示力量,需要一种更加多样、灵活、广撒网式地展示力量,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地进入盟国和友邦的新地方。这在这些地区的国内政治中是非常有争议的。所以即使在像日本这样非常亲密的盟国那里需要用到新的地方,当地民众对这种事总是感到不高兴。所以我们需要在政治层面非常谨慎地管理这些关系。韩国正在经历政治过渡,他们是亲密的盟国。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保持敏感。我担心的是,我们对这些经济体提出的关税已经冲击了他们的汽车产业,在“关税解放日”90天暂停结束后这一冲击会更加严厉。
主持人: 在美国公路上真的有很多日本和韩国汽车。
柯庆生: 当然,它们非常受欢迎。其中一些是在美国生产的,所以它们不算,但即使在这里生产,我们还是需要进口零件。
主持人: 是的。
柯庆生: 关税会使那些零件变得更贵。如上所述,它影响到国内政治。当你试图与盟国和友邦做新的事情的时候,经济层面的摩擦会使其寸步难行。我认为我们在国家安全领域做得很好。我们发现中国的崛起对区域安全构成了真实的挑战。我们需要战略性地竞争。我了解有关它的一切并支持它。我希望看到它与我们的经济政策更紧密地结合,因为如果它们不结合,经济战略造成的政治摩擦有可能削弱对我们在安全方面的政策支持。
主持人: 除了结束这些关税,减少经济摩擦,我们还能做什么来让我们的盟国安心?我们还能做什么?
柯庆生: 我认为我们管理负担分配的方式也很重要。我欣赏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能让欧洲人在国防上投入更多预算,我认为这很重要。我期望亚洲盟国和友邦在国防上花费更多,但我认为他们应该更多地认同对我们之间的联盟关系的力量和耐久性。我相信我们与中国在该地区的竞争战略有一个受到冲击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在俄乌冲突政策上的逆转,东亚的盟国和友邦对我们对待乌克兰的方式感到震惊。
主持人: 您的意思是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会极大地影响盟国对我们的印象?
柯庆生: 就是他们如何真正地看待我们,看美国有多可靠。最近,韩国和台湾进行了民调,当问到这些地方的公众如何看待美国的安全承诺,他们对美国的信任因为华盛顿俄乌战争政策的转变而大幅度下降。还有第二个方面,拜登政府在其四年任期内在加强美国和东亚的联盟方面做得很好。但他们还做了另一件事,那就是不仅加强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这主要是俄国入侵乌克兰导致的,而且他们还让东北亚国家,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相互合作,这是很卓越的一步,是每届的政府都希望看到的,而且它还让韩国和日本与北约盟友合作,让韩国和日本领导人参加北约会议。
北约盟友已在东北亚设立办事处与这些国家加强联络。这很重要。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联系对美国在亚洲的威慑力很重要,因为欧洲国家不太可能在危机或冲突中向东亚投射重要的军事力量,但它们对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在经济上非常重要,这样中国在使用武力时不仅可能导致其使用武力的目标和美国以及可能一两个其他盟友的军事反应,而且还可能导致东北亚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反应。欧洲人正在成为遏制中国使用武力的主要力量。我现在担心的是,就像一些美国战略学者在讨论国际地缘政治时所说,我们对待乌克兰的方式以及我们对两个联盟体系的离间使得一旦中国动武就可能出现的经济制裁变得不那么可能。我也认为对欧洲和东亚国家施加的关税可能使美国更难在未来团结各国对中国使用武力做出经济制裁。我担心北京动武的胆量会因此变得更大。
主持人: 沿着这些思路,柯博士,我想问你,印太盟国和友邦是否欢迎对中国竞争的单一关注,并且在对北约和乌克兰的支持上花费更少的资源?还是说,他们把北约和乌克兰看作是他们未来的预兆,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
柯庆生: 是的,我认为这比他们对我们专注于中国或东亚感到宽慰更复杂。我确信,通过与台湾的讨论,他们非常支持乌克兰对俄国的反抗,因为他们把它看作是某种东西的前车之鉴。他们把它看作是美国和欧洲支持民主国家对抗威权的表示。台湾几乎整个政治光谱上的人都是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这里牵涉到一个动态的逻辑,这种类似物理学的逻辑告诉我们,如果美国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消耗有限的弹药,或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消耗有限的国防资金,那么给台湾这样的地方的武器和国防资金就会更少。这是有道理的,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士气是威慑和人们的认知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说,如果台湾人民希望我们支持乌克兰,那为了支持台湾的防务而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似乎就得不偿失了。一个又一个对台湾的研究表明,台湾的士气和为自己的防务挺身而出的意愿与他们眼中美国的可信任度是直接相关的。如果台湾人民看到美国出卖了乌克兰,那么美国的可信任度就会受到质疑,那么我们出售给台湾的武器的数量可能没有我们伤害的士气多少那么重要。韩国和日本也是如此。这是他们能够克服彼此历史上的摩擦并与美国一起三边合作的几个原因之一。这是拜登政府在戴维营会议上取得的一个真正的突破,即这两个国家不仅为俄国入侵乌克兰感到恐惧,中国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让他们感到更加恐惧。
俄乌战争侵犯民主国家的主权,这一侵略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必须克服历史摩擦。乌克兰在某种程度上是韩日安全考量的中心。我认为他们对华盛顿乌克兰政策的转变感到震惊。是的,它确实为亚洲战区释放了更多的潜在资源,我认为这很重要。很多深思熟虑的制造武器的计划都很好,因为印太战区需要更多的武器。

主持人: 也需要更多的舰船。
柯庆生: 我们需要更多的舰船,我们需要更多的远程打击武器,我们需要将它们部署在战区,以便它们及时起到威慑作用。这些我都明白,我也知道到世界上美元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我认为我们对乌克兰的政策是我们在与中国竞争中最大的优势,虽然它给我们(在亚太)的盟国和友邦造成了一些真实的伤害,即便乌克兰距离亚太战区很远。美国在支持乌克兰方面付出了重要资源。
主持人:柯博士,我们密切关注和了解另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那就是关税。美国和中国是真的在较劲。如果这些关税持续下去,美国对中国的高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我主持另一个叫《贸易人》(The Trade Guys)的播客节目,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个话题。我真的很想知道你认为关税会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柯庆生: 我不想给你可能从很多嘉宾那里听到的不疼不痒的答案,那就是这个事因具体情况而定,但它确实取决于具体的情势。我听过《贸易人》播客,很棒。
主持人:谢谢夸奖。
柯博士:真的很棒。现在还很难预测(最后的)关税率会是多少。我们有个90天的暂停,但它们仍然相当高,非常高,正如你在上次播客所阐述的。人们谈论的是30%的税率,但此外还有预先存在的关税,所以加起来可能更高。真的很难弄清楚,但如果90天过去了,根据各种信号,税率会变高。当然关税也可能会降下来。如果关税在135%,中国人会失去美国市场,这对中国的经济将是非常有害的。
中国正尝试在他们的经济战略中做准备,无论在内销还是在对其他国家的外贸。出口对中国经济很重要。在过去几年中,它们比以前更重要。中国不完全依赖出口。我认为这在人们的讨论中有些夸大了,但他们确实有一些非常劳动密集的行业依赖美国市场。所以他们会失去很多工作岗位。出口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变得更加重要。在过去几年,中国的经济更多地依赖出口增长,比他们在前几年依赖得更多,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推动内消作为增长动力方面遇到了困难。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房地产一直低迷。在某种程度上,它似乎在恢复,但这是因为中国家庭,特别是城市里的家庭,大多将他们的大部分储蓄投在房地产中。所以如果你的主要资产价值在缩水,你在消费方面会变得更加保守。
主持人: 他们自己不消费,因此出口变得更加重要。
柯庆生: 2024年发生的事情不同凡响。中国与世界的贸易顺差超过1万亿美元,这是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我认为中国专家和外国专家都同意这个观点。我不是经济学家。我不会假装自己是经济学家。你的播客节目上有非常好的经济学家,我听他们的讲话并从他们那里学习。但中国专家和外国专家都会同意中国需要一个由消费驱动的经济体才能长期发展。我认为他们也同意,尽管让中国专家大声说出这一观点很难。2024年的战略是不可持续的,世界无法消费中国出口的商品。所以当我之前说这取决于美国关税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会利用其对第三国的关税筹码让它们改变自己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我认为中国可能能够承受美国的关税。它会造成很大的失业,中国已经有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这对中国来说不会是一个愉快的时光。但如果美国能让像越南或墨西哥或其他国家减少它们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那么,这对中国经济来说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的整个增长模式虽然不像有时描述的那样依赖出口,但它约占其GDP的20%。所以2018年后发生的事情非常有启发性。美国第一轮大规模关税生效后,我就预测到可能发生的事情。美国继续消费了几乎与关税前一样多的价值的中国产品,从美国与世界整体贸易逆差的百分比来看的确是这样。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但美国与越南的逆差和与墨西哥的逆差飙升了。在越南,它从2018年的每年350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每年1250亿美元。墨西哥,它从2018年的每年800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1800亿美元。从这些国家进口的产品的大部分是中间产品,它们来自中国,再在这些地方进行最终组装。这些公司中的很多不全是中国公司。这些事情很复杂,它涉及到我们与盟国和友邦关系的优质问题。我去年休假时去了11个国家,也去了越南。越南人在2024年11月(美国)大选之前,已经对美国的保护主义和它可能的走向感到十分紧张。
他们担心的原因之一是像三星这样的韩国手机公司过去在中国制造制造手机。现在三星在越南制造超过80%的手机,而这些手机的大部分零件来自中国。手机不过是在越南组装,然后再送到美国消费者手中。越南人当然担心美国加征关说。所以当我之前说对中国的影响因情况而定。美国能否让像越南、柬埔寨、泰国、孟加拉国、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因为美国以自己的市场对它们的关闭迫使它们减少与中国的合作?也许吧?我认为这是一个艰难的赌注,因为这些国家非常依赖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所以说,如果所有的筹码都到位,中国经济可能会受到严重伤害。但我认为系统性地实现越南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脱钩将是非常困难的。真的很困难。
主持人: 有趣的是中国抗衡美国的筹码和我们正在发展对付他们的筹码之间的互动。《纽约时报》写道,我们的汽车制造商用完了磁铁,它们都来自中国,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可能没有飞行需要的零部件了,因为他们也需要这些的磁铁以及许多其他与稀土有关的部件。我想问你的问题是,我们总是认为中国领导人独裁,对中国人民有完全的控制。现在会有一些人质疑他的领导力吗?
柯庆生: 我认为中国领导人是列宁主义组织的领导者,我认为这些类型的组织总是担心国内的稳定。我们作为外人可以看到一个没有明确的对手的非常强大的领导者,但担心国内不稳定有点像是列宁党的DNA。他们担心国内不稳定的方面之一是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沮丧。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因为这些国际事件而下滑,这会是一个挑战。但我认为我们近期内看不到会有人挑战中国的领导人。他可能担心失业吗?他可能担心中国已经存在的青年失业吗?他担心房地产行业吗?我可以确定地说他担心,因为这些人就是这样运作的。他们更担心的是国内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的安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工作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重心。所以,是的,他们会担心这个。美国能否通过关税政策改变中国国内政治?我对此有强烈的怀疑。他们会担心这些结果吗?这是很可能的。回到我们与盟国和友邦的关系,如果所有这些国家都是跨国生产链的一部分,这就是东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与其他地方的相互依存的模式真正的不同之处了,它们是跨国生产链的一部分。如果中国零件在其他国家被组装成最终产品并被送往世界各地,那么这些国家将非常关心美国关税。中国,尤其是如果它被一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事情所改变,即对来自中国以外各国的进口商品进行检查,就可以确定最终产品中中国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主持人: 所以美国希望在产业链中绕开中国?
柯庆生: 是的,美国是否能做到这点正是人们正在关注的。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意识到了这一点,理解问题的所在,因此正在尝试解决它,只是这件事的决策非常非常复杂。它会非常刺激,并且它可能在与正在向美国出口并受到美国这种进口监督的国家的关系中造成真正的摩擦。这可能使美国与韩国这样的国家产生真正的摩擦。韩国有两个潜在问题。一个是他们在韩国制造的产品。他们在韩国制造的许多汽车的重要零部件要从中国进口,包括与稀土相关的材料。他们已经受到高汽车关税的冲击。如果还要加上他们因为汽车有中国零件而受到更高的关税冲击,他们会忧心忡忡。
我去年在韩国时听说了这种担忧,我认为日本也是如此。在像三星这样在越南制造大量产品的韩国公司肯定是这样,因为美国对越南加征46%的关税,如果90天的关税暂停没有产生积极的结果,那这对韩国公司、日本公司和已经将生产地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等地的美国公司将是非常有害的。其中一些伤害在这一切发生前就开始了。其中一些开始只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变得越发昂贵,让公司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但我认为这一过程多半是被2018年关税和对未来关税的恐惧加速了。
主持人: 以及拜登政府继续实施关税的政策?
柯庆生: 是的,他们根本没有降低它们。我的意思是,乔·拜登做候选人时反对关税,说它们对美国消费者的伤害很大,但他在任上不但没有取消任何关税,还顺便增加了一些新的关税。
主持人: 柯博士,这真是一个你在CSIS的精彩开场。您的观点很引人入胜。非常感谢您,我真的期待着更多这样的对话。
柯庆生: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