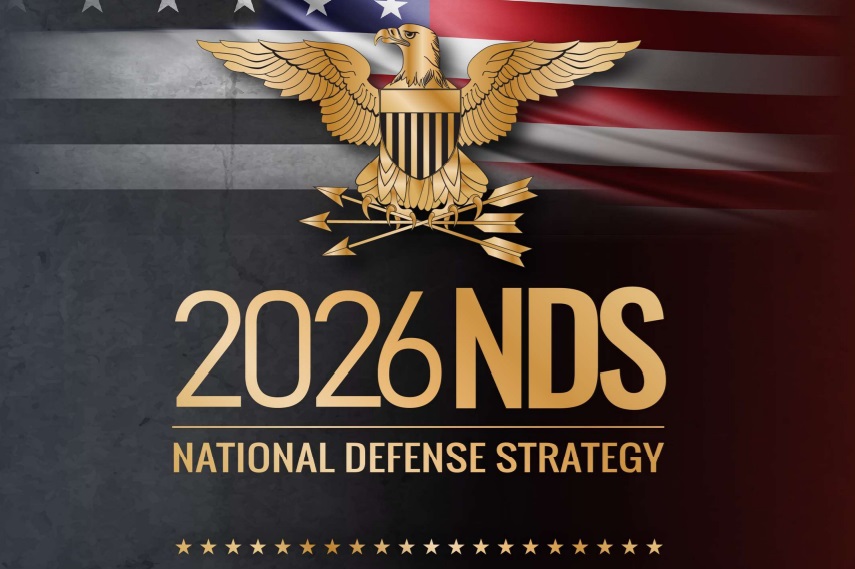外媒:“国家资本主义”?特朗普工业政策能否成功?
- 编译
- ZHANG Juan
- 19/10/2025
- 0

《华尔街日报》:特朗普式国家资本主义?
《华尔街日报》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特朗普政府的工业政策越来越像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篇文章提到,自由市场失灵是美国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
文章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公众和两党普遍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失效,美国不可能涉足国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鼓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CEO将生产转移到海外,结果是制造业劳动力萎缩、关键矿产等重要产品对中国产生依赖,以及对清洁能源和半导体等未来产业投资不足。
这篇文章写道,特朗普的做法并不是没有先例。联邦政府历来会介入企业事务:二战期间,它曾调配生产资源;在《国防生产法》框架下,也曾在新冠疫情等紧急情况下进行干预;在2007-09年金融危机期间,它救助了银行和汽车公司。然而,这些干预多为临时性措施。
前总统拜登则走得更远,试图塑造产业结构。《通胀削减法案》授权提供4000亿美元清洁能源贷款,《芯片与科学法案》划拨390亿美元补贴国内半导体制造。其中,85亿美元拨给英特尔,这给特朗普提供了杠杆,让他以英特尔前CEO与中国的关系为由要求其下台(英特尔迄今拒绝)。
拜登曾推翻美国钢铁公司管理层和股东的意愿,阻止日本制铁收购该公司,尽管其团队认为交易不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特朗普则推翻了这一否决,并获得“黄金股”,可以用来影响公司决策——无论在设计还是命名上,这都模仿了中国民营企业向中共发行的“黄金股”。
拜登官员曾考虑设立主权财富基金,以资助战略性高风险项目,例如中国主导的关键矿产领域。而上个月,特朗普国防部表示,将持有关键矿产开采商MP Materials 15%的股份。
文章分析,许多西方观察者钦佩中国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和对重点产业的扶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能力。而美国的努力往往因多元民主制度下的制衡与妥协而受阻。作家丹·王在其即将出版的著作《破局:中国工程未来的探索》中写道:“中国是一个工程型国家,以惊人的速度推进大规模建设;相比之下,美国是律师型社会,尽其所能阻碍一切,无论好坏。”
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他的魅力在于敢于推倒这些“律师式”的障碍。他通过对多个国家和行业征收关税,攫取本应属于国会的权力,并声称将亲自指导来自日本、欧盟和韩国的1.5万亿美元投资承诺,尽管在法律上似乎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这些承诺本身也存在争议)。
文章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此前鲜有成效,因为国家无法比私人市场更高效地配置资本。通常会产生扭曲、浪费和裙带关系。俄罗斯、巴西和法国的发展速度都远低于美国。
事实上,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成功。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指出,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市场驱动,而非国家力量。随着习近平重新加强国家控制,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中国储蓄充裕,但国家浪费严重,从钢铁到汽车,产能过剩导致价格和利润暴跌。
美国的情况也不佳。以国家安全或扶持新兴产业为名的干预,往往导致投资失败,例如威斯康星州富士康工厂或纽约布法罗的特斯拉太阳能工厂。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全民参与、由北京通过地方政府干部和企业董事会全面掌控的体系,而美国的做法大多停留在白宫的声明上,缺乏政策和制度框架。诺顿指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纪律,而特朗普完全相反。”
国家资本主义不仅是经济工具,也是一种政治控制手段。习近平通过经济杠杆压制任何威胁党的统治的行为。例如,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在2020年批评中国监管机构扼杀金融创新,结果遭到迅速打击。蚂蚁集团首次公开募股被叫停,公司最终因反竞争行为被罚款28亿美元,马云短暂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特朗普同样通过行政命令和监管手段,对媒体公司、银行、律师事务所以及他认为反对他的企业进行打压,同时奖励与其政策一致的高管。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CEO们若对其移民或贸易政策持异议会公开发声,而现在他们大多向他捐款或保持沉默。
特朗普还试图对长期独立运作的机构施加政治控制,如劳工统计局和美联储,这与中国官僚体系完全服从党的领导有相似之处。
特朗普一直钦佩习近平对国家的掌控能力,但理论上,美国仍存在制约。美国民主通过独立司法、言论自由、正当程序以及多层级和多部门权力分散,对国家行为形成制衡。国家资本主义在美国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取决于这些制衡机制能否有效运作。
卫报:经济学家分析美国制造业能否回流?
与此同时,《卫报》的一篇报道认为,虽然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激烈的贸易政策正在为美国制造业复兴铺路。然而,在白宫之外,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
全球贸易专家指出,总统推行的关税政策可能无法带来制造业的显著复苏,原因包括政策反复无常、关税范围零散,以及特朗普取代前任政府“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后,以强硬手段应对全球贸易伙伴。
“我认为这些关税会削弱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并减少就业机会,”保守派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经济学家迈克尔·斯特雷恩(Michael Strain)说,“它们提高了美国制造商的生产成本,使其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下降。虽有少数受益者,但输家数量将远超赢家。”
特朗普及其助手坚称,对100多个国家征收更高关税、抬高进口成本,将刺激国内制造业。白宫发言人库什·德赛(Kush Desai)宣称:“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美国制造’将重拾全球主导地位。”
但学界普遍对此持怀疑态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前院长安·E·哈里森(Ann E. Harrison)指出,特朗普关税政策反复无常,政策的持续性和可预测性不足,已几乎注定了大规模制造业投资浪潮难以实现。
她对《卫报》表示:“要想成功,政策必须长期一致。企业需要相信它会持续。许多工厂规划和建设周期长达五年,但特朗普不断改变主意,过去六个月几乎没有出现一致性。”她还指出,总统年纪较大,也让企业对政策延续性产生疑虑。
此外,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今年5月裁定特朗普的全面关税存在违法之处,虽然目前仍在上诉中,但这一裁决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不确定感。斯特雷恩表示:“反复无常、合法性存疑、未经国会批准,这些都让企业难以决策。即便有‘协议’,也并非真正约束性协议。”
拜登政府则采取更具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来推动关键产业发展,如半导体和电动汽车。通过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对锂电池征收25%关税,以及提供购买补贴和建设工厂的资金支持,美国新建半导体、电动汽车及零部件工厂数量大幅增加。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表示:“如果想增加制造业和就业,应针对特定领域制定产业政策。全面关税在激发投资方面效果有限。”哈斯商学院的哈里森指出,成功的产业政策应鼓励竞争,而关税恰恰可能限制了竞争。
凯斯西储大学经济学家苏珊·海尔珀(Susan Helper)也认为,特朗普对欧盟、日本和韩国征收的15%关税过低,难以吸引企业为规避关税而在美建厂。“半导体工厂投资数十亿美元,需要多年回报。低税率难以支撑投资决策。”
白宫宣传与欧盟、日本、韩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包括巨额投资承诺,总额超过1.5万亿美元。但经济学家质疑,这些承诺是否具有约束力。哈佛大学罗德里克表示:“这些大数字更多像装点门面,是随意抛出的整数。”罗斯福研究所贸易专家托德·塔克(Todd Tucker)指出:“部分投资是企业原本计划进行的,部分只是愿景。等实际投资发生时,特朗普可能已进入下一个新闻周期。”
近年来,制造业就业人数持续下降,不仅在先进工业国家如此,在中国也因新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哈里森指出,美国制造业已过巅峰期,“我看不到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或就业人数会逆转。”
AEI的斯特雷恩表示,对钢铁和铝征收高关税虽能保护个别生产岗位,但会伤害下游使用钢铁的就业岗位。他引用美联储研究指出,特朗普首任期内的关税实际上与全国工厂岗位减少相关。
海尔珀警告,特朗普的政策可能让美国汽车业陷入“落后的孤岛”。她说:“我们可能在大型、耗油皮卡车上占优势,但在电动汽车领域进一步落后。这条道路既冒险又危险。”
总的来看,学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关税虽意在振兴制造业,但在政策不连贯、投资承诺可疑、全球技术趋势及自动化背景下,其实际效果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