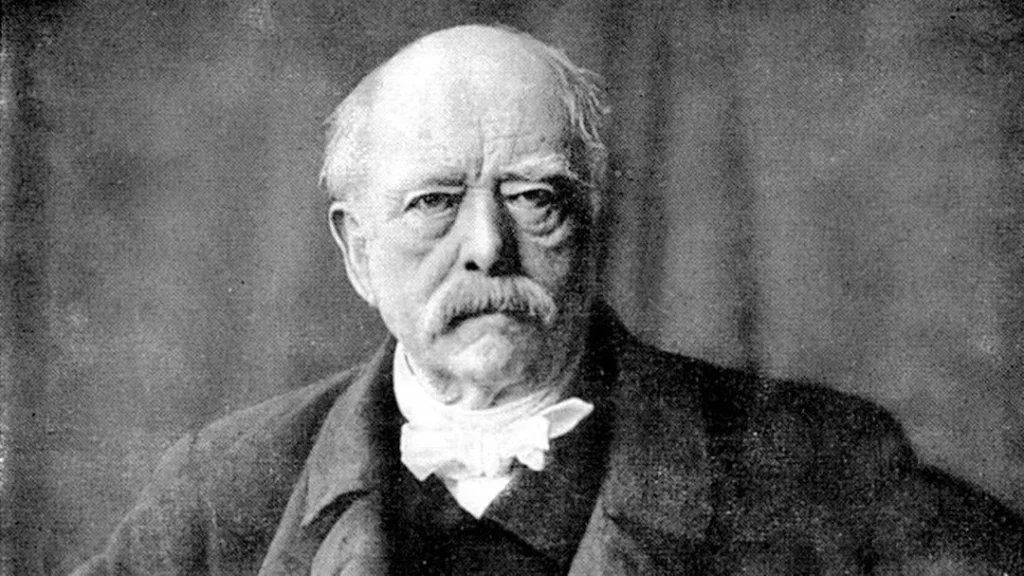李巍: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的打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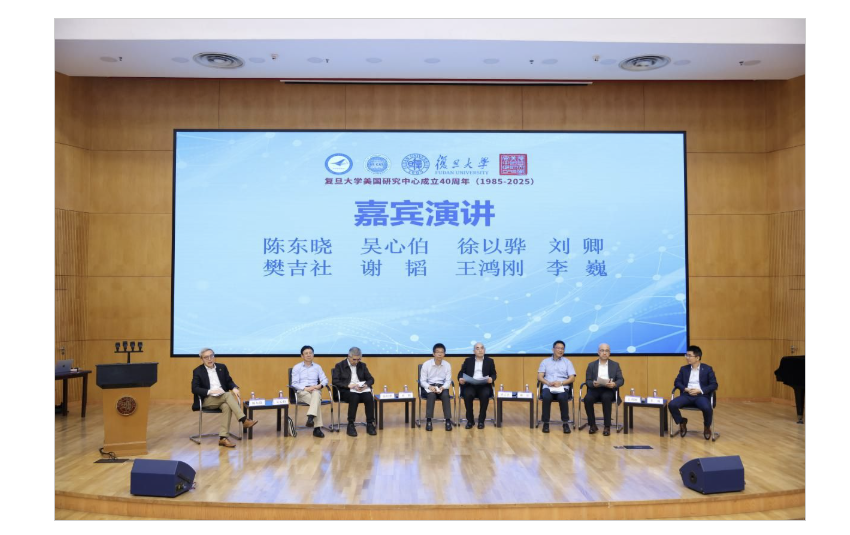
过去的三个世纪,我们目睹了人类经济史上出现了三个“世界工厂”,分别是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和21世纪的中国。德国和日本虽然也曾拥有过强悍的制造能力,但因为多种结构性的缺陷,不能称之为“世界工厂”。中国在201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并在此后15年的时间里不断拉开与美国的差距,这是21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
这一事实在美国产生了四个极富冲击力的后果。第一,制造业的衰落全面破坏了美国的产业生态系统,直接约束了美国在多个方面的创新能力。因为创新不能仅仅在实验室里诞生,它需要大量的应用场景,才能跨越从技术到产业的那个“死亡之谷”,所以转移低端,保留高端,其实是不成立的,就犹如一片森林,离开了低矮灌木,也难以长出参天大树。 第二,制造业的衰落影响了美国的军工产能。在过去三年的俄乌战争中,尽管俄罗斯在战场上的表现难堪亮眼,但美国也难以支撑这场长期的资源消耗战,这也是特朗普为何急于结束这场战争的原因之一。第三,制造业的衰落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税收能力。如今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就像一个巨大的堰塞湖,它只能靠美元霸权所提供的“掠夺性”的融资能力在勉强支撑,而从长期来看这无异于饮鸩止渴。第四,制造业的衰落导致“铁锈地带”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加剧了美国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的垮塌,而强大的中产阶级是美国民主的“稳定器”,因此,它影响了美国民主制度运行的质量。
美国新一代的战略家杰克·沙利文用“掏空”一词,来形容中美的产业竞争关系。为此,他提出了“新华盛顿共识”的理念,号召美国要全力开动国家机器而不再是通过全球市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全面复兴美国本土制造业,修复美国的产业生态系统。经过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任美国总统的动员和实践,美国形成了产业复兴的国内共识和系统的产业战略思想,这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最连贯一致的国家大战略。
自2018年3月开始,美国对华经济战争螺旋式上升,这是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围绕“世界工厂”地位所展开的一场剧烈博弈,它事关美国霸权的存亡绝续。美国动用关税武器挤压“中国制造”的市场空间,目前美国对华平均关税高达50%以上,这导致仅在8月份中国对美出口就同比下降33%;美国动用技术武器限制中国的产业升级,今年以来中国C919飞机交付量不及预期,就是其中的后果,那就更不用提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所面临的艰难处境;美国还动用金融武器削弱中国企业的融资能力,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融资额与美国存在着云泥之别,仅占美国的1/10左右。
中国的制造业崛起源于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市场、技术和金融等关键资源,现在美国要做的就是要全面推倒那个对中国相对最为有利的经济全球化。
应对美国打压中国“世界工厂”的唯一方式就是扩大开放。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把中国打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只有内循环的封闭经济体,进而大幅抬高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而我们则需要反其道而行之。1846年,英国在理查德·柯布登的领导下废除了《谷物法》,彻底走出了重商主义的泥淖,全面奔向自由贸易,1851年,伦敦举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象征着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到来;1934年,美国通过了《互惠贸易法》,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扛起了自由贸易的大旗,随后美国赢得了二战。在过去的几个月,美国先后与欧盟、英国、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达成贸易协议,对其加征的10%和15%的对等关税被制度化,战后历经多轮谈判所达成的自由贸易成果付诸东流,国际贸易体系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大国,如果中国逆势而动,加快与这些国家推动更低关税的自由贸易谈判,甚至大胆采取更多单边开放政策,比如像过去一两年来我们所采取的单方免签证政策,那么美国的关税最终孤立的只能是他自己,而中国则会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赢得全球治理中的引领地位。
9月27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了成立40周年的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李巍在会上做了题为《工业与霸权》的发言。以上为他的发言稿的总结。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基地对他的发言进行了总结,中美印象再此基础上进行了排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