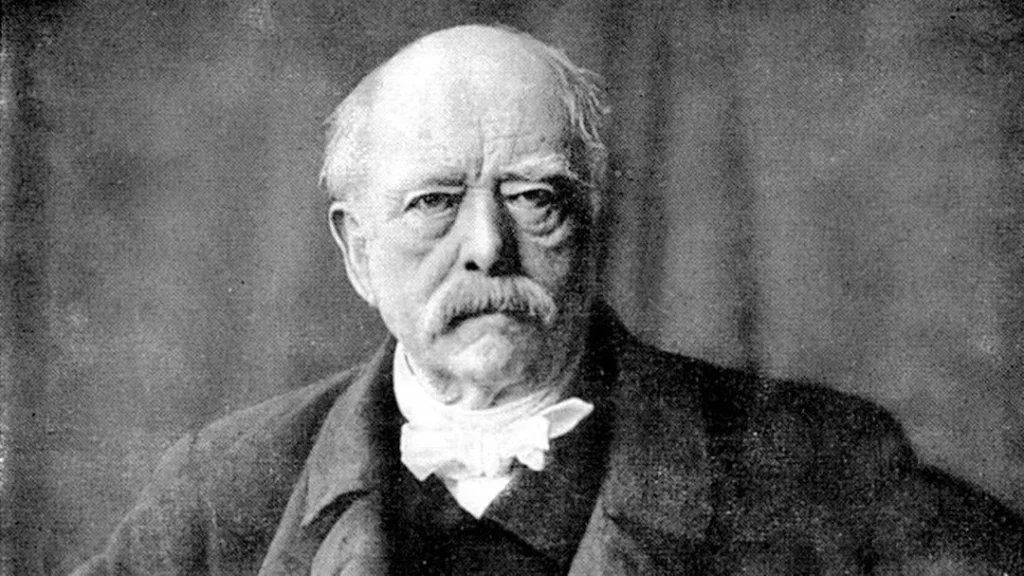社评:“印太经济框架”难以遏制中国
作者:胡志勇 来源:中评社
拜登上台以来,频频出台针对中国的政策,以全方位遏制中国发展。“印太经济框架”即为其中之一。“印太战略”需要经济层面的合作作为支撑,美国急需创立一个经济框架吸引部分国家加入“印太战略”,今年5月,拜登在日本高调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印太经济框架”以互联经济、弹性经济、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四大支柱为框架,美国通过建立“印太经济框架”,力图推进半导体等的供应链强化、跨境数据流程通的规则制定等。在数字经济、劳工和环境等重点领域制定规则与标准。该框架聚焦贸易、供应链、基础设施、去碳化、税收和反腐败等主要支柱领域,旨在深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建立“互联、清洁、公平、有韧性的经济”。美国企图在亚太地区建立排他性的供应链系统,重整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领导力”,以实现美国的战略意图。
“印太经济框架”14个创始成员国基本都是中国的地理周边和“大周边”国家,东盟十个成员国中,印尼、新加坡、泰国、越南、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七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该框架。
“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重树信誉的重要手段。美国试图利用这一框架重塑地区经济格局,对冲和降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对现有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经济合作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加大了这些东盟国家在中美两国竞争中选边站队的战略压力和现实困扰,破坏并进一步离心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合作氛围;在东亚,美国试图联合日本、韩国等,在全球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晶片供应链体系。在提升日、韩等盟国高技术合作的同时,不断恶化中国的周边环境,引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高新技术竞争,削弱和降低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
美日在技术和经济层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从冷战时期的传统盟友转型为一种专注于科学、技术创新结成更紧密的新型战略伙伴同盟,双方将合作范围拓展至军事、经济、前沿技术等多个领域,以及研发、供应链、建立标准等多个层面。对全球科技创新版图和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影响深远。美日务实合作将进一步损害中日关系,恶化东亚安全环境。
而且,美日联手推动关键技术国际标准制定,以主导全球数位经济规则的制定。美日合作建立“6G”无人化技术国际标准和数据跨境传输标准,增强己方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竞争力,在印太经济框架下,联手在印太区域推广。美日借“印太经济框架”进一步发展双边防务技术研发合作,以应对高超声速武器和天基打击能力威胁,提高空中作战效能。
美国积极拉拢台湾,并将其纳入晶片“四方联盟”之中,在控制全球晶片供应链体系把中国大陆排挤出晶片供应链体系之外同时,进一步破坏台海关系,阻挠中国和平统一事业。
“印太经济框架”在涉及高科技产业所需的矿产供应链方面,美国将构建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体系,并建立预警机制。推动与中国供应链“脱钩”基础上的排他性合作,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该体系一旦建成,将冲击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品产业链的布局,影响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矿产品的有效供应。
美国从全球化的宣导者变成全球化的破坏者,试图以价值观为由建立排斥中国的平行体系。“印太经济框架”即是美国这一战略思维的具体体现。美国积极利用该框架在各领域建立高标准规则,借此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为中国经济发展制造更多障碍,以打压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并干扰和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
“印太经济框架”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其实质是在地缘经济领域与中国展开错位竞争,以主导印太地区发展进程,但难以建立实效性合作。
首先,印度以其在该经济框架中看不到好处为由,第一个退出了“印太经济框架”相关贸易谈判,给美国泼了一盆冷水。
其次,日本政府内部对“印太经济框架”也有冷淡的看法。
第三,受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美国在东南亚的投资倡议难以落地实施。
第四,地区国家对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态度较为谨慎,由于该框架没有将市场准入纳入其中,部分成员、尤其是东盟国家的谈判动力会有所不足。现有的“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显然是更优框架。
第五,“印太经济框架”不同于自贸协定。自贸协定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推行贸易自由化,属于市场的效率导向;而“印太经济框架”基于战略性贸易理论,重视政府合作,属于国家的安全导向。“印太经济框架”祗有规则谈判,不包括货物贸易、服务投资、政府采购等市场准入谈判,战略性产业的合作,一般属于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但“印太经济框架”约束力有限。由于数字经济、劳工、环境、清洁能源等领域的谈判具有一定难度,“印太经济框架”取得进展的可能性较小。
尽管如此,“印太经济框架”将进一步加剧中美战略性产业的技术竞争,提升美国在未来全球贸易与供应链体系中更多的话语权,削弱和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毒化中国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政策,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动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竞争政策等各项政策与国际通行规则的接轨,在供应链领域,包括出口管制、制裁、供应链合作等方面建立多边国际规则,强化与主要经济体的政治关系、加强与其供应链合作;进一步健全相关法规体系,积极探索建立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规则、数据保护能力认证规则、跨境数据交易规则,并有序扩大重点领域开放,加快自主创新,逐步提升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
来源时间:2022/9/17 发布时间:2022/9/17
旧文章ID:28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