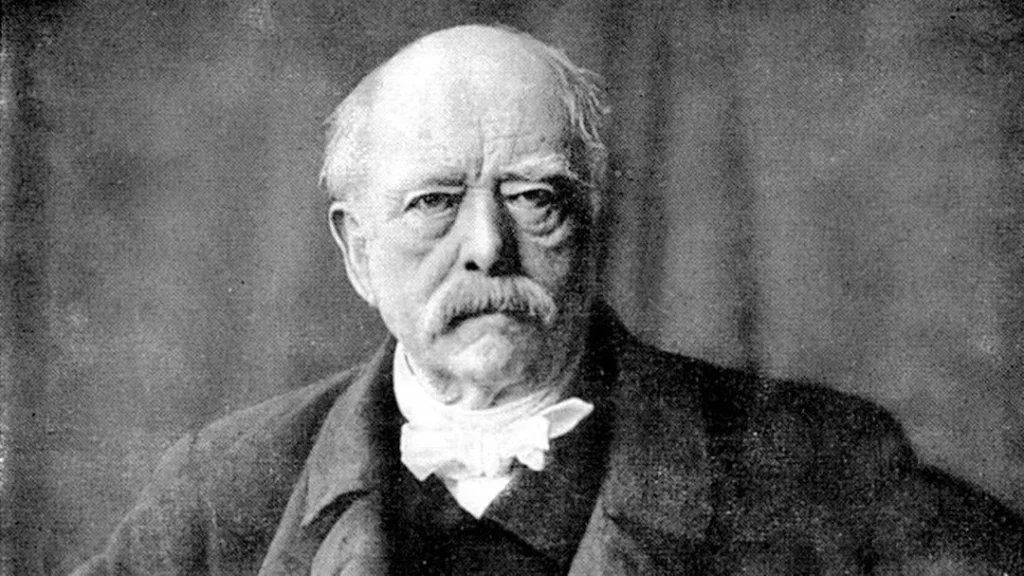赵穗生:特朗普2.0,另类鹰派?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曾在2025年1月达沃斯论坛的一场小组讨论中打赌:“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会对美中关系的改善感到惊讶,因为习和特朗普相处得很好,彼此了解。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伟人,在这方面,他们惺惺相惜。”
欧亚集团创始人伊恩·布雷默作为同一场讨论的嘉宾则强烈反驳,并表示,12个月后美中关系很可能“实质性恶化”,因为中国坚信美国在遏制中国。“尽管特朗普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中国的能力与意图并不支持这一点。”
如今,特朗普2.0政府已执政半年,艾利森与布雷默的判断均未完全应验。美中关系既未出人意料地改善,也未发生实质性恶化。
在2017年以前,在接触政策之下,美中关系常处于“倒退/危机—巩固/前进”这种周期性循环之中。然而,在特朗普1.0时期,这一模式被以地缘政治竞争、(两国对对方的)幻想破灭及意识形态敌意为特征的长期危机所取代。这场危机并非由突发事件或美国总统选举周期引发。目前,尽管美国外交政策存在高度分化,但在对华立场上已形成新的两党共识:即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2018年至2023年间,美中关系经历了持续螺旋式下滑,跌至历史低点。大量官方沟通渠道瘫痪。2018年10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访华遭冷遇后,美国内阁成员基本停止访华;与此同时,民间交流大幅减少,媒体报道以负面渲染居多,进一步加剧误解和敌意。
当中美军机军舰在台湾海峡、南海和东海频繁接近之际,拜登总统担忧意外冲突的发生,提出重启沟通渠道并建立“护栏”,以负责任地管控竞争。
北京同样不愿两国陷入不可控的危机。2022年11月,拜登与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期间会晤,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在2023年初访华。然而,由于中国气球事件,布林肯的访华被推迟至6月。此后,美国接连派出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气候特使克里、商务部长雷蒙多四位高官访华,并于11月15日在旧金山举行“习拜会”,为两国关系“筑底”。虽然峰会带来缓和氛围,但长期危机并未根本缓解,双方仍在台湾、贸易、南海等敏感议题上相互碰触红线。
我在近期文章中指出,中美双方对彼此的意图、政策与底线了解得太多,以至于难以真正相信对方的承诺。在步入大国竞争新时代后,双方都难以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或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缺乏信任基础。而台湾问题,更是中美最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核心议题之一。
特朗普不是传统对华鹰派
特朗普更像是一名贸易强硬派和交易推动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鹰派。他主张在经济和贸易上对华强硬,但并非以全球领导地位为目标。他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意识形态输出。
特朗普经常将新冠疫情、经济混乱和芬太尼等问题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并试图在政治话语中妖魔化中国。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几乎未对中国提出地缘政治层面的批评。他没有提及南海,也未对中菲海上冲突表态,最引人关注的是,他没有为台湾“仗义执言”——这是历届国会两党几乎必表忠诚的议题。
特朗普以个人利益和交易考量为驱动,而非原则、条约或国际规范。他并不热衷于维护全球秩序或捍卫远方盟友。他关注的是国内“敌人”——非法移民、恐怖分子、“觉醒左翼”、以及性少数群体。他倡导搁置意识形态分歧,与其他大国共同对抗自由主义价值观,并毫不犹豫地削弱美国对外事务机构,如解散国际开发署,退出世卫组织、巴黎协定、人权理事会等。
即便特朗普的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在国会一贯强硬批评中国人权,他仍终止了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局(DRL)的大量资助,而该局一直是对华人权倡议的主要资金来源。
特朗普2.0时期,几乎没有延续1.0政府的对华鹰派班底。蓬佩奥、博明、博尔顿、黑莉、史迪威等人均未入阁。2025年5月,国家安全委员会裁撤超百人,其中包括十余名负责中国事务的关键人员,如东亚事务高级协调官大卫·费斯、亚历克斯·王等。这些人员的流失削弱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连贯性与执行力。
特朗普设想的是一个强人政治主导的世界格局:大国间达成“势力范围”的默契与合作。他的“美国优先”战略体现为一种新门罗主义式的大陆主义。《纽约时报》曾刊文《特朗普的愿景:一个世界,三个强国?》指出,特朗普或许期望与中俄形成某种合作框架,由美主导西半球、中主导亚太、俄主导欧亚大陆。
他的国务卿鲁比奥进一步明确这一世界观,宣称美国的单极时代已结束,当下世界正回归一个多极大国并存的格局。美国冷战后的霸权只是短暂的历史例外。然而,特朗普的实用主义和交易倾向并未缓解中美间的结构性冲突,反而为大国竞争增添新的不确定性和动荡。
中美竞争走向何方?
这场长期危机正将中美两国推向格雷厄姆·艾利森所描述的“修昔底德陷阱”。虽然结构性矛盾根源于权力转移,但领导人的决策与战略选择同样决定着竞争是否会升级为冲突。
北京在大国竞争初期犯下了一些因自信与冒进导致的战略误判。之后则在不断调整,力图应对“美国既是经济机遇也是安全威胁”的复杂局面。美国同样失误频频,低估中国韧性、夸大中国威胁,从而导致反应过度。其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会导致地缘政治竞争升级,引发本可避免的冲突;阻碍正常的学术与人员交流,令对华裔的歧视悄然蔓延;加剧科技、贸易冲突,带来巨大经济代价;激发中国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又反过来强化中国的“本土创新”战略。
最后,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中美竞争是否可能有“赢家”?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博弈,双方都无法赢得最终胜利,但也都输不起。
中国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大国。其政权性质是否长期存在虽无定论,但美国及其他外部力量都不可能改变中国的制度走向。阻碍中国继续崛起的,只有中国自身。美国仍是全球最强国家,凭借其地理、科技和制度优势长期保持韧性。尽管多次陷入危机和动荡,但总能自我调整、恢复元气。那些宣称“美国衰落”的声音,最终大多被现实打脸。
正因为谁也无法取代谁、谁也无法改变谁,中美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和平共存。这不仅是竞争理性的体现,也是现实的需要。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疾病防控、经济相互依存等领域,都要求中美合作。
结构性与意识形态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关键在于领导人是否有远见与理性,愿意超越零和思维,寻求共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