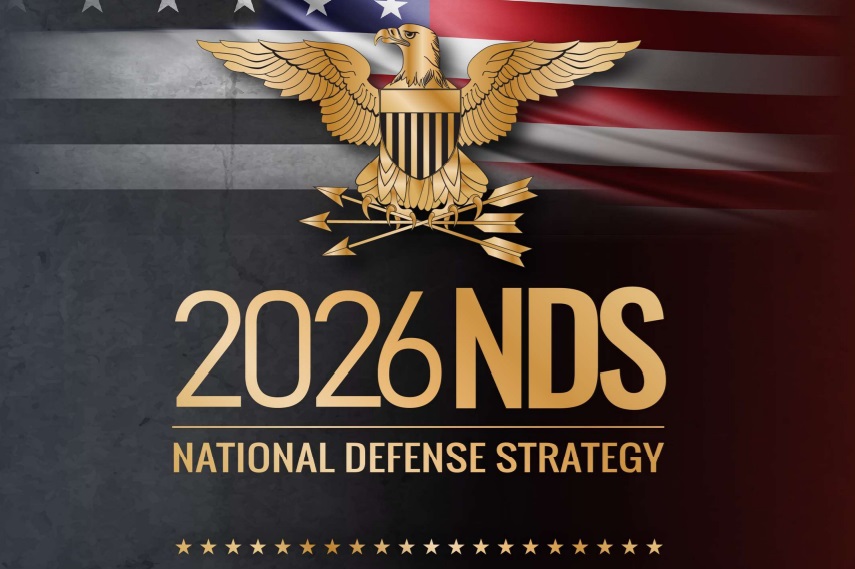应对中国,美国应该期待欧洲做什么?

【编者按: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9月11日发表了题为《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欧洲如何融入美中战略竞争》的报告。该报告邀请了六位学者以小短文的形式回答了三个大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是:1,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应该向欧洲寻求或期待什么?2,在跨大西洋关系出现明显裂痕的情况下,中国为何对欧洲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北京希望通过与欧洲大陆的接触达到什么目的?3,欧盟如何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定位自己?布鲁塞尔认为哪种美-欧-中关系最符合欧洲的长期利益?我们今天为读者发表了学者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乔纳森·A·琴(Jonathan A. Czin,布鲁金斯研究员)
坦白说,考虑到目前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对欧洲的期望不应太高。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在许多曾有深入合作的关键领域大步倒退,比如放松了部分高科技出口管制、淡化人权问题,并从台湾问题上退缩。这两种趋势无疑都缩小了双方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一致的余地。
尽管如此,我依然对许多欧洲领导人就中国带来的挑战持续发出清晰的声音感到惊讶。例如,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在七国集团(G7)会议上,就曾公开谈及中国在稀土磁体领域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风险。虽然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和观察家对欧洲在对华合作上的犹豫感到失望,但如今看来,欧洲已经不大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对华一味迁就的政策。北京自身的行为,尤其是其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支持,已经让欧洲各国的立场变得强硬。这表明,只要华盛顿能重拾更严肃的对华竞争姿态,美欧在对华问题上依然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丹尼尔·S·汉密尔顿(Daniel S. Hamilton,布鲁金斯非驻会研究员)
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对中国抱有共同的担忧。他们对北京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帮助莫斯科规避西方制裁感到愤怒。他们对中国的网络盗窃、知识产权侵犯、未能充分履行世界贸易组织(WTO)义务,以及许多行业因国家补贴导致的产能过剩感到沮丧。他们担心北京会利用其对欧洲经济至关重要材料的控制,并且对中国在欧洲战略产业的投资保持警惕。此外,他们也批评中国的人权侵犯、对香港的收紧控制、对台湾的威胁姿态,以及对欧洲贸易关键海上航道的争夺。欧盟领导人对中国高达3500亿美元的对欧贸易顺差深感不安。2025年7月的欧中峰会气氛紧张,最终成果只有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
然而,跨大西洋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一致仍旧困难,部分原因是欧盟27个成员国并非总能步调一致。尽管许多国家已转变为对华强硬派,但仍有一些国家将经济机遇放在首位。此外,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对欧洲经济已至关重要。欧洲人也担心,那些被美国市场拒之门外的中国产品会转而倾销到欧洲。
迈克尔·E·奥汉隆(Michael E. O’Hanlon,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
首先,从一个消极的角度看,美国不应该奢望,也肯定不应该期待,欧洲能在与中国的任何冲突中提供多少直接的军事援助。但美国可以希望,当美军专注于亚洲的冲突时,欧洲盟友能基本靠自己来应对欧洲的安全危机。例如,在当前背景下,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欧洲要在没有太多美国帮助的情况下,维持乌克兰的主权并保护北约的东翼,特别是在小而脆弱的波罗的海地区。
此外,我曾在2019年的著作《钓鱼岛悖论》中提出“综合威慑”战略,这与前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后来在国防部所倡导的理念相似。根据这个战略,欧洲应该继续监测并减少其对中国的经济和战略依赖。我们的目标是避免在安全危机中被中国勒索,并能在西太平洋发生战争时,与华盛顿携手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经济战工具可能是以可接受的条件结束冲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在这方面,作为一个联盟,我们需要在事态升级中对北京保持主导地位。
另外,或许这有些异想天开,但如果欧洲富有创造性的地缘战略家们能找到一个台湾和中国都能接受的未来“统一”方案——至少是某种邦联安排——那将是极好的。我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假设我们能用目前的政策和工具轻松地处理台湾问题(尽管我支持“双重威慑”政策,将其视为可预见未来的次优选择)。由于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被认为历史包袱较轻,他们可能比美国更有能力在时机成熟时发起这场辩论。
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
美国和欧洲在对华问题上最重要的合作,是如何在全球化经济中应对中国这个前所未有的制造业巨头。美欧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应该共同努力,重塑全球贸易、金融和公司治理规则,从而为减少利益冲突和保护主义、实现更广泛的增长以及为负面外部性承担责任奠定基础。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中国,也必然会触及国内治理,无论是在民主还是非民主制度下。为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各国都必须牺牲部分主权并承担一定的依赖风险,正如自现代商业出现以来它们一直在做的那样。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因此,我希望欧洲能继续成为全球化的有力旗手(尽管有许多言论,但全球化不会成功逆转),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围绕规则和公平建立共识。经济交流本质上是一种双赢的互动,也让参与者有继续保持关系的动力。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化,而不是更少,但我们也需要承诺更好的规则、更好的执行以及更好的外交。我希望欧洲能继续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坚持不懈。
塔拉·瓦尔马(Tara Varma,布鲁金斯访问学者)
欧洲在应对中国挑战时,必须既要考虑其与美国关系的演变,也要独立于美国行动。跨大西洋关系的深刻转变已经让人们对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的可靠性产生了疑问。在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背景下,欧洲明白自己不能简单地用对另一个国家的依赖来取代在安全上对华盛顿的依赖。
因此,美国必须为欧洲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方式做好准备,这些行动可能与美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例如,欧盟的数字法规可能会导致对TikTok的禁令,而这几乎没有与华盛顿进行任何协调。
尽管在对华问题上存在跨大西洋分歧,但欧盟和美国此前已设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轨迹达成共识,这部分是在美欧对华对话期间形成的,最近一次对话是在2024年9月举行。这些旨在制定对华共同行动计划的交流尚未在“特朗普2.0”政府下恢复。随着美欧中三方战略竞争的加剧,对美国和欧盟来说,分享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对华政策,仍然符合双方的利益。
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
美国应该希望欧洲在对华关系中捍卫自己的利益,并通过欧盟以统一的方式共同努力。欧洲对中国采取了更具竞争性的立场,这并非为了帮美国的忙,而是因为这符合其自身利益,也因为北京的策略实在过于拙劣。美欧在对华政策的每个细节上不会总是意见一致,但如果欧洲的方针是统一且具有战略性的,那么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立场将大体上保持一致。反之,如果它们内部出现分歧和混乱,那么跨大西洋关系将出现严重背离。
在某些领域,美国应该与欧洲人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举两个例子:他们应该就如何应对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挑战达成共识,包括产能过剩、对关键矿物的过度依赖,以及如何确保企业能在北京的非市场竞争行为下保持竞争力。他们还应该在技术上更紧密地合作,包括美荷在半导体领域的持续合作,以及共同管理人工智能的风险和机遇。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传递出的信号是,它对跨大西洋在对华问题上的合作并不那么感兴趣。这不意味着欧洲会转而支持中国,但许多潜在的合作机会将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