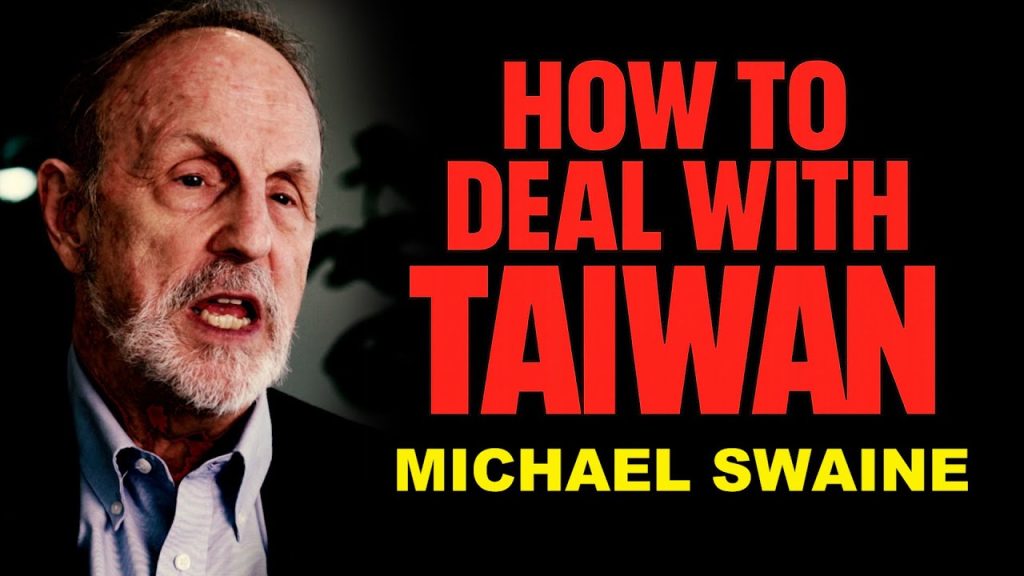惠顿关于台湾的主张过于极端且逻辑不通

今年八月,美国前总统布什与川普政府时期的资深顾问克里斯蒂安·惠顿(Christian Whiton)在 Domino Theory 平台发表了两篇涉台评论。惠顿自称为“台湾的长期支持者”,却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外来处方色彩的建议,包括:将台湾防务“以色列化”、加大无人机与新兴技术投资、去除“中华民国”象征以重塑身份,以及推动台湾金融体系的激进自由化。然而,台湾的战略道路必须立足自身历史与民主体制,培育内生性的社会韧性,而非依赖外部的处方性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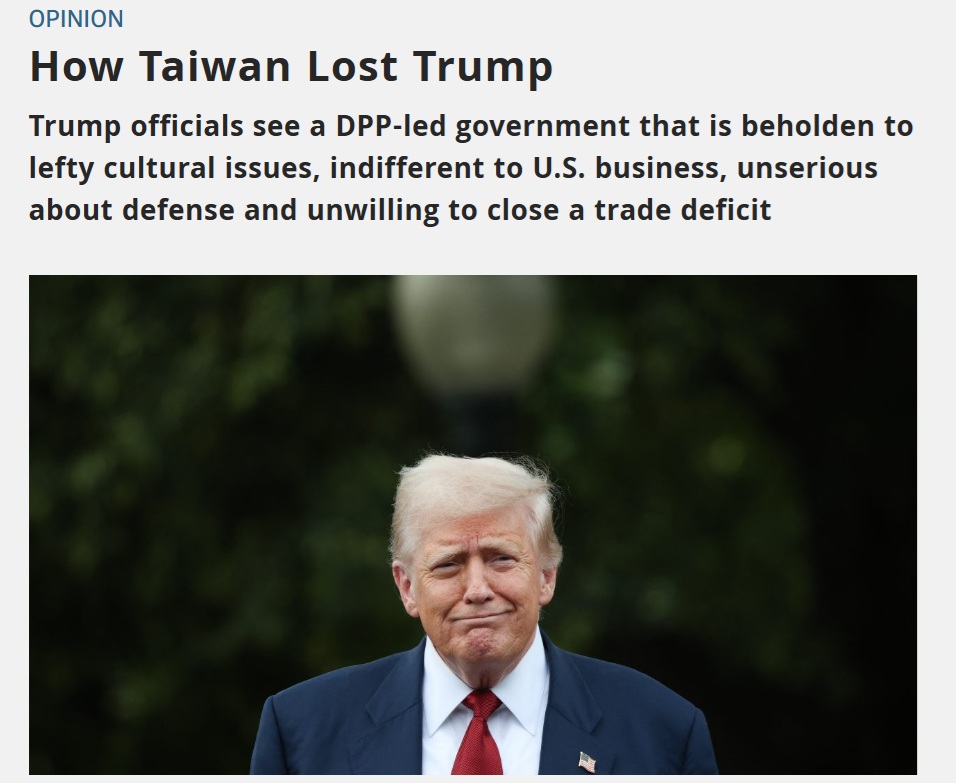
谬误之一:将台湾防务“以色列化”
惠顿呼吁台湾实行全民皆兵,并将军费开支提高至GDP的10%。然而,这一建议无视台湾的社会现实、简化了台湾的历史经验,也忽略了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台湾与以色列的安全处境存在根本差异。
以色列人口约一千万,仅为台湾的一半,国土面积狭小(22,072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新泽西州),四周被敌对邻国环绕。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至少经历了七场大规模战争,与阿拉伯世界的宗教与资源冲突至今未解。这种敌对环境迫使以色列实施全民役制,将其视为国家生存的必要手段。
相比之下,台湾虽承受来自中国大陆的军事压力,但整体安全环境相对稳定。中国大陆是唯一的不确定因素,而这种威慑多停留在“灰色地带”,未突破全面战争的门槛。外交层面上,台湾拥有更广泛的区域合作网络,并通过美日同盟间接获得安全支撑。这意味着台湾并不面临以色列式的“生存困境”,也无迫切必要照搬以色列防务模式。
此外,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长期承受威权统治与“白色恐怖”的创伤记忆,社会普遍珍视个人自由与宪政民主。全民皆兵若作为激进措施推行,势必引发民意反弹,破坏政府与社会的互信。事实上,自2024年以来的两轮“罢免潮”已表明,台湾民众更强调社会团结而非过度军事化。
经济层面的“枪炮与黄油”矛盾同样凸显。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Ryan Hass)指出,台湾当下面临的重要挑战在于就业与财富分配,而非军费不足。2024年民调显示,49.1%的民众支持扩军,43.8%反对,社会分歧显著。财政现实更使惠顿的建议难以立足:2025年台湾国防预算为GDP的2.45%,维持债务比率24.9%的同时,社会福利开支仍占最大比重(2024年为21.3%,2025年为26.5%)。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已在2025年3月明确表示:“中华民国在目前阶段绝对没有能力”将军费提高至GDP的10%。与之相比,新加坡虽实施全民役制,但军费维持在3–5%之间,越南役期长达24个月,但始终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置于首位。这些经验共同说明:中小国家的韧性源于安全与民生的平衡,而非极端军事化。
结论很清楚:台湾需要的是“国防韧性”,而非全民皆兵。安全来自繁荣与社会稳定,而非过度的军备扩张。惠顿的“以色列模式”缺乏社会与经济支撑,终究难以落地。
谬误之二:去除孙中山与“中华民国”符号
惠顿建议台湾移除孙中山与“中华民国”符号,以重塑国家身份。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华民国与台湾民主发展的历史联系,也贬低了这些符号在台湾社会身份建构中的作用。
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后,中华民国宪法与五院制成为台湾治理架构的制度基石。尽管国民党一党专政备受批评,但这一体制同时为台湾的民主化与经济起飞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在对外领域,“中华民国”仍是台湾的正式称呼,被广泛用于国际交流,并已嵌入台湾社会的认同体系。
孙中山与蒋介石两位人物也深刻影响了台湾的政治文化。蒋介石主导了“375减租”“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为台湾农业现代化与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战后长期作为教育与宪政合法性的核心内容,被纳入学校必修课程直至1980年代。尽管其被批评为威权工具,但“三民主义”思想本身也提供了民主宪政的理念延续,并启发了台湾本土民主先驱如蒋渭水。这表明,台湾的身份转型是一个渐进演化的过程,而非与中华民国的彻底切割。
因此,惠顿要求台湾切割孙中山与中华民国身份,既忽视历史复杂性,也否认了台湾民主化的演进逻辑。这一主张如同要求美国因建国者曾蓄奴而推翻宪法、剔除所有英国文化遗产,逻辑上站不住脚。尊重历史而非抹去历史,才是台湾民主未来的根基。
谬误之三:金融自由化的幻想
惠顿主张台湾全面自由化金融体系,效仿“新加坡/迪拜模式”。然而,这一设想脱离了台湾的社会经济现实。
台湾长期重视社会公平与稳定。财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台湾基尼系数为0.272,处于亚太最低水平之一。相比之下,美国约为0.41,新加坡约为0.35,而阿联酋更高达0.63以上。经验表明,激进自由化往往带来财富高度集中,削弱社会公平与制度合法性。
台湾产业结构同样不支持迪拜式模式。2022年,台湾服务业占GDP的61.72%,半导体产业占22.6%。半导体作为支柱产业,使台湾对资本流动与市场波动格外敏感。激进金融开放不仅难以带来稳定增长,反而可能引发资产泡沫与社会撕裂。
区域案例更具启示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与韩国因过度自由化受到重创;反观越南自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虽积极吸引外资,但保留对关键行业的管控,至今国企仍贡献超过四分之一GDP。这种渐进式改革有效避免了社会动荡。新加坡的成功依赖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而台湾多元民主不具备复制条件。
因此,台湾的最佳路径是“稳健型开放”——在保障金融活力的同时兼顾社会韧性,而非盲目照搬外来模式。
比较分析与结论
新加坡、越南与台湾同为中小型经济体,处于美中竞争的夹缝,既是“摇摆国家”,也是“前线国家”。三者人口介于600万至2300万之间,经济高度依赖出口,政治体制兼具国家能力与社会约束。共同的儒家文化底色则强化了稳定优先的社会取向。在此背景下,惠顿的方案更像是一种美国视角的映射,而非根植于东亚现实的策略。
台湾的真正优势在于“竹子外交”与“韧性社会”:既能随风而动,又有深厚根基;在“枪炮”与“黄油”之间不断调整,以维持长远的战略平衡。
台湾从未“失去”川普或任何外国政治人物。其竞争力根本不依赖外部认可,而在于基于本土优势的不可替代性。真正的战略成熟,不在于取悦大国领袖,而在于打造一个自由而坚韧的社会。唯有如此,台湾才能在大国竞争的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倒。
作者
-

徐宇深是本站特约撰稿人,曾在卡特中心和亚洲协会实习。